

Citation: Zuzheng He, Hui Liu. Application of Macrocyclic Compounds as Drug Solubilizers[J]. Chemistry, 2021, 84(5): 426-432, 425.

大环化合物作为药物增溶剂的应用
English
Application of Macrocyclic Compounds as Drug Solubilizers
-
Key words:
- Host-guest system
- / Macrocyclic compounds
- / Solubilizer
- / Inclusion complex
-
药物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取决于药物的水溶性、渗透性、溶出度、首过效应、对外排机制的敏感性等参数,其中药物的水溶性是影响口服生物利用度的重要参数[1]。一方面,大多数生物膜都覆盖着粘液等水基外层,只有可溶的药物分子才能渗透到膜上;另一方面,较差的水溶性会阻碍口服固体剂型药物的吸收,并限制其注射用、眼用等溶液剂型的配制[2]。目前有许多方法可以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水溶性,例如添加助溶剂或表面活性剂,调节pH,药物成盐,制备水溶性配合物等[3]。
环糊精(CDs)、杯芳烃(CAs)、柱芳烃(PAs)、葫芦脲(CB[n])等大环化合物由于能通过非共价作用将大小合适的药物分子包裹于其结构的中心空腔中形成包合物,使得其作为增溶剂改善难溶性药物水溶性的潜力巨大[4]。难溶药物与主体分子可以通过相对较弱的非共价作用(如氢键、范德华力、静电作用、偶极作用、疏水作用等)结合在一起[5]。由于包合物的形成是动态可逆过程,因此可以在不影响客体生物活性的情况下提升其水溶性[6],在增溶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药物溶出度、稳定性等性质的改善,进一步提升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本文首先介绍CDs、CAs、PAs、CB[n]几种大环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和结构特点,然后综述了近年来大环化合物作为增溶剂在药物增溶领域的研究及应用进展,最后对其在实际应用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1. 环糊精
CDs属于第二代超分子大环化合物,为α-1, 4-糖苷键连接的吡喃葡萄糖单元组成的环状低聚糖,是由细菌降解淀粉而形成的天然化学物质。根据吡喃葡萄糖单元的数量,天然CDs可分为α-CD、β-CD和γ-CD,分别含有6个、7个和8个吡喃葡萄糖单元[7](图 1)。它们在空腔大小、水溶性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表 1列举了它们的一些理化性质。
图 1
表 1
α-CD β-CD γ-CD 空腔直径/Å 4.7~5.3 6~6.6 7.5~8.3 空腔体积/Å3 100 160 250 腔内水分子数 2.5 5.0 8.5 水中溶解度/(mol/L) 0.12 0.016 0.17 溶解吉布斯自由能/(kJ/mol) 15 20 14 CDs“内疏水、外亲水”的独特结构使其对难溶性药物具有包合和增溶作用[8]。在水溶液中,亲脂性药物分子可以进入CDs的疏水空腔,形成水溶性包合物,还能进一步改善药物的稳定性、溶出速率等[9]。
1.1 α-CD增溶剂
三种CDs的空腔尺寸各异,α-CD的内腔直径为4.7~5.3 Å,比β-CD和γ-CD小得多,但是α-CD的溶解度适中,25℃下的溶解度约比β-CD高7.5倍,比γ-CD低1.4倍[10]。另外,α-CD的安全性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证为相对更高。
硝酸益康唑(ECN)是一种咪唑类抗真菌药,主要用于治疗皮肤感染,但是极低的水溶性限制了其对生物膜的渗透能力。Jansook等[11]发现,CDs可以有效改善ECN的溶解度(图 2),在酸性条件下,α-CD (5(w/v)%)将ECN的溶解度从0.4mg/mL提升至3.0mg/mL,γ-CD(5(w/v)%)也使其溶解度上升至0.8mg/mL。体外活性测试还表明,α-CD的包合作用使ECN的抗真菌活性得到有效增强。α-CD的空腔和ECN尺寸更加匹配,相比之下,γ-CD的空腔太大,难以和ECN分子匹配。1H NMR分析也证实,ECN的疏水部分更有效地插入α-CD空腔中,显示了疏水键在增溶中的作用。
图 2
1.2 β-CD增溶剂
β-CD是目前研究最广泛的药物载体之一[12],尽管其自身的水溶性较差,但它的空腔直径(6~6.6 Å)是容纳大多数化学物质的理想尺寸[13]。为了改善β-CD的水溶性,研究者制备了羟丙基(HP-β-CD)、磺丁基(SBE-β-CD)、甲基(M-β-CD)等官能团化衍生物。修饰后的衍生物不仅保留了空腔特性,还拥有了极佳的水溶性;基于β-CD衍生物的药物增溶剂往往还能改善药物的稳定性等其他属性,目前已应用于临床给药[12]。
HP-β-CD是欧洲药典和美国药典收录的药用辅料,目前已有多种以其作为增溶剂的市售药物,包括脑血管药丁苯酞氯化钠、抗真菌药物伊曲康唑、抗精神病药物利培酮、激素类药物左甲状腺素钠等。官能团化带来的生物相容性和水溶性(>500g/L)的提升,大大改善了β-CD的增溶能力。醋酸地塞米松(DMA)是一种肾上腺皮质激素药,常用于局部透皮给药,但其低水溶性影响了其治疗浓度。Vianna等[14]分别制备了DMA/β-CD和DMA/HP-β-CD的包合物,结果显示,DMA的水溶性分别提升了48倍和88倍,稳定性分别提升了5倍和12倍。β-CD能很好地包裹药物分子,但增溶能力受到了其自身水溶性(0.16g/L)的限制,而高水溶性的HP-β-CD在增溶时具有更明显的优势。此外,DMA稳定性的提高可能是因为易水解的酯基部分被封闭在CDs的空腔中,从而阻止了水分子的进攻。
SBE-β-CD是β-CD的羟基被磺丁基取代的衍生物,按不同的取代度可分为单取代、多取代和全取代β-CD。药用辅料Captisol是以1, 4, 7-磺丁基取代为主成分的SBE-β-CD。已经使用Captisol技术上市的药物包括抗精神病药物甲磺酸齐拉西酮、抗真菌药物伏立康唑、NK1受体拮抗药马罗吡坦、抗精神病药物阿立哌唑、广谱抗病毒药物瑞德昔韦等[15]。瑞德昔韦的剂型为注射剂和冻干粉针剂,由于其几乎不溶于水,因此两种制剂的配方中均含有Captisol作为增溶剂[16]。Williams等[17]选择不同的增溶剂通过薄膜冷冻工艺开发了瑞德昔韦干粉吸入剂,结果显示,基于Captisol的剂型不会影响其物理和化学稳定性,同时可有效改善瑞德昔韦的溶解度(提高了20倍)。另外,体内药代动力学显示,基于Captisol的剂型具有更快的初始全身吸收,反映了Captisol技术的巨大优势。
离子化CDs在与带相反电荷药物作用时往往更具优势[18],如图式 1所示,Fenyvesi等[19]用氨基和琥珀酰基对M-β-CD进行修饰,分别得到了带正电荷的MA-RAMEB和带负电荷的Su-RAMEB。引入离子基团后,CDs的增溶能力会根据不同电荷的客体而发生改变。对于电中性的胆固醇,离子基团的空间位阻使M-β-CD的增溶作用下降。对于阳离子药物如碘胺酮和他莫昔芬,电负性的Su-RAMEB的增溶能力最佳。带正电荷的MA-RAMEB是阴离子药物呋塞米的最佳增溶剂,增溶效果为非取代的M-β-CD的3.5倍。然而,与中性M-β-CD相比,当主体与客体所带电荷相同时反而会使主体的增溶能力下降。这说明主客体之间的静电作用是包合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因此在增溶离子药物时,可以在增溶剂中设计并引入相反电荷的离子基团来提高增溶能力。
图式 1
1.3 γ-CD增溶剂
与天然α-CD和β-CD相比,γ-CD具有最大的疏水空腔(7.5~8.3 Å)和最高的水溶性。γ-CD非常柔软,可以被人唾液酶或胰淀粉酶快速消化,较高的溶解度和有利的毒理学特性使其成为药物增溶剂的最佳CD候选物[20]。
Uekama等[20]研究了α-CD、β-CD、γ-CD对黄体酮、孕酮等18种甾体激素的增溶作用。结果显示,γ-CD对类固醇分子有优异的增溶能力,而α-CD对许多类固醇分子没有增溶作用,这可能是α-CD的腔体尺寸较小,类固醇分子几乎无法进入。与类固醇分子的主客体结合强度顺序为γ-CD>β-CD>α-CD,表明CDs的空腔越大,对类固醇分子的包合越容易。
1.4 环糊精增溶剂的应用前景
目前全球约有30多种药品使用CDs作为增溶剂。由于其价格低廉、经济易得,它已成为制剂工业中药物包合的首选试剂[21]。不同结构的CDs在增溶时各具优势。α-CD的腔体尺寸较小,但是其水溶性适中,安全性相较更高;β-CD的腔体尺寸最佳但水溶性低,然而修饰后不仅水溶性得到提升,取代基的多样性也赋予其包裹不同性质药物的独特优势;γ-CD更大的空腔决定了其在包裹较大的药物分子时有更高的亲和力。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CDs作为药物辅料的安全性[22],其中HP-β-CD和SEB-β-CD是经FDA批准的药用辅料[23],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安全性研究,并且具有高水溶性、强包合能力和低肾毒性。但是,α-CD和M-β-CD在非肠道给药时都表现出肾毒性[24]。β-CD由于能与胆固醇形成复合物而引起肾毒性,使得其不适用于肠胃外给药的剂型[25]。综合看来,CDs优异的增溶能力、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安全性使得其在药物增溶领域拥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2. 大环芳烃
杯[n]芳烃(CAs)属于第三代超分子大环主体,是一类具有可变数量的苯酚单元的大环化合物,苯酚单元通过邻位的亚甲基桥连而成环状结构(图式 2)[26]。所有的CAs都有一个三维空腔,可以包合尺寸匹配的客体分子,空腔大小取决于苯酚单元的数量[27]。
图式 2
CAs能够以类似CDs的方式包合水溶性较差的分子[28]。由于CAs易合成、易修饰的特点,研究者开发了磺化杯[n]芳烃(SCXn)[29]、氨基化杯[n]芳烃(CALIX)[28]、磷酸化杯[n]芳烃[30]等高水溶性衍生物应用于药物增溶领域。
柱[n]芳烃(PAs,n=5~10)属于第五代超分子大环主体,是一种具有独特柱状结构的大环主体(图 3)。由对苯二酚单元组成并通过对位亚甲基桥连接,与CAs组成相似,但立体构型不同[31],富电子的对苯二酚单元使腔体对缺电子的客体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图 3
 图 3. 典型柱[n]芳烃的结构和模型[34] (n=5~10)Figure 3. Structural and cartoon representations of typical pillar[n]arenes (n=5~10)
图 3. 典型柱[n]芳烃的结构和模型[34] (n=5~10)Figure 3. Structural and cartoon representations of typical pillar[n]arenes (n=5~10)PAs易官能化的特点使得其能够调节与客体的结合作用。阴离子(羧酸盐)[32]或阳离子(铵盐)[33]修饰的水溶性PAs的成功制备拓展了其药物增溶的潜力。
2.1 磺化杯[n]芳烃增溶剂
已知的水溶性CAs中SCXn具有最高的水溶性(>0.1mol/L),内表面和磺酸基团分别为疏水和亲水分子提供作用位点,富电子且柔软的三维空腔使得其能够通过非共价键与众多药物分子作用[35]。
Yang等[36]研究了SCXn对肠驱虫药烟酰胺(230ng/mL)水溶性的影响,发现增溶作用会受到主体空腔尺寸的影响(结构见图式 3)。增溶能力顺序为SCX6(7.6Å)>SCX8(11.7Å)>SCX4(3.0Å),与烟酰胺的结合常数大小为SCX6(3.92×103L·mol-1)>SCX8(1.46×103L·mol-1)>SCX4(1.38×103L·mol-1),说明SCX6的空腔尺寸和烟酰胺可能更为匹配。热分析实验和相溶解度实验显示,与SCXn的酚羟基形成的氢键为包合提供了最主要的贡献,其次是由于烟酰胺高度疏水,当处于极性介质(水)中时,极性介质会将其“挤出”,导致烟酰胺与SCXn疏水空腔产生更强的疏水作用。
图式 3
图式 4
2.2 氨基化杯[n]芳烃增溶剂
CALIX的结构和化学组成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杯芳烃分子的边缘可被相同或不同的氨基完全或部分取代,亚甲基桥的自由旋转使其没有空间位阻,构象呈多样性[37]。
Ukhatskaya等[28]研究了CALIX对抗真菌药物克霉唑的增溶能力,并和SBE-β-CD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CALIX使克霉唑的溶解度提升了21000倍,增溶效果明显优于SBE-β-CD(溶解度提升了490倍)。这可能是因为电离后的CALIX具有表面活性剂的性质,可以在水中聚集,因此增溶能力大于常规CDs。
2.3 磷酸化杯[n]芳烃增溶剂
磷酸化CAs衍生物的毒性较低,对人成纤维细胞的生长没有影响[30]。且许多药物结构中含有氨基,使得磷酸化CAs作为药物增溶剂具有一定优势[38]。
Bayrakci等[30]合成了5种不同结构属性(空腔尺寸、所带电荷等)的磷酸化CAs,选取呋塞米(38μg/mL)、烟酰胺(230ng/mL)、硝苯地平(5~6 μg/mL)三种模型药物研究影响CAs增溶能力的因素。磷酸化CAs作为增溶剂可以使呋塞米的溶解度提升至(6.22~10.11)×10-3mol/L(约54.1~87.8倍),烟酰胺的溶解度提升至(2.72~4.37)×10-6mol/L(约1.4~2.3倍),硝苯地平的溶解度提升至(4.72~11.2)×10-5mol/L(约3.3~7.8倍)。进一步研究显示,CAs的增溶能力主要取决于的疏水空腔的直径、CAs与药物分子间的静电作用、氢键等。
2.4 柱[n]芳烃增溶剂
羧酸化的PA[6]细胞毒性低、生物相容性高[39],同时,大空腔(6.7Å)、高水溶性、优异的主客体识别能力、简单易合成的特点使其在药物增溶方面颇具研究价值[40]。
为了提升抗肿瘤药物的溶解性,Yu等[41]设计合成了含有苯丁酸氮芥(Cbl)和荧光生色基团(Py)的抗肿瘤前药(Py-Cbl,见图 4),并选用高水溶性的羧酸化PA[6](WP6)提高其溶解度。主客体包合不仅使Py-Cbl的溶解度提升了110倍以上,WP6空腔还保护了Cbl的酯基被水解,从而有效降低了降解速度;同时,由于Py的引入,可以在紫外光的照射下实现精确可控的药物光响应释放。MTT试验结果显示,包合作用还降低了Cbl的细胞毒性,有效减少了其对健康组织的副作用。
图 4
2.5 大环芳烃增溶剂的应用前景
α、β、γ-CD的内腔直径在4.7~8.3 Å左右,而且CDs是非常刚性的[42];而CAs、PAs类的大环芳烃内腔直径是可变的(3.0~11.7 Å),且柔性空腔增加了包合药物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还没有对大环芳烃进行药用辅料的毒理学评估,美国FDA目前尚未批准其在制剂中使用[30]。CAs的毒性主要受修饰基团的影响,因此可以相应地进行调节[43],并且大多数CAs是没有毒性的。PAs的毒性研究还不够充分,但已研究的羧酸化PA[6]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目前,大环芳烃毒理学评估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随着衍生物的发展和毒理学评估的深入,其作为增溶剂的应用一定有良好的前景。
3. 葫芦[n]脲
葫芦[n]脲(CB[n]=5~8,10,13~15)属于第四代超分子大环化合物,是由亚甲基连接的甘脲单元组成的南瓜状分子容器[44](图 5)。CB[n]具有疏水空腔和亲水性羰基边缘的刚性结构[45],在水溶液中,CB[n]与客体分子的结合常数较高,通常在106~109 L·mol-1之间[46]。在已知的CB[n]中,CB[7]具有良好的水溶性(20~30 mmol/L)[47],毒理学研究也证实了CB[7]的生物相容性[48]。
图 5
但是CB[7]也有局限性:一是刚性结构限制了其可封装药物的尺寸[49];二是较强的结合作用使得包合后的药物解离缓慢[50];三是化学修饰困难[46];四是其自身水溶性低[51]。
Ma等[52]为了克服CB[n]的局限性,设计并合成了两种开环CB[n]型主体作为药物增溶剂(图 9)。相较传统CB[n],其优势在于优异的水溶性、包合难溶性药物的能力以及可快速、完全释放客体药物分子。新型开环CB[n]包含一个中间的C型甘脲四聚体,提供疏水空腔,边缘脲基单元促进阳离子结合能力,末端芳香环可与不溶性药物进行π-π堆积,四个取代磺酸基使得CB[n]的水溶性增加。
3.1 葫芦[n]脲增溶剂
CB[n]的疏水空腔和高电负性的羰基使得其可以通过离子-偶极作用和疏水作用包合各种有机或无机分子,客体的进出受羰基入口和空腔大小的控制。氯法齐明(CFZ)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推荐使用的抗麻风病药物,但是长期高浓度服用会产生心脏毒性并导致皮肤色素沉淀、腹痛等。Li等[53]使用CB[7]配制CFZ的水溶液,使得原本在水中几乎不溶的CFZ溶解度提高到1.5mmol/L;而且在斑马鱼模型体内评估时发现,包合后CFZ的心脏毒性明显减轻,且体外对结核分枝杆菌的杀菌效果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3.2 开环葫芦[n]脲增溶剂
开环CB[n]的构象比传统刚性CB[n]分子更灵活,其稠合多环骨架能像手一样弯曲以容纳更大的客体,这扩大了其包合药物的范围[54]。相较刚性CB[n]与客体的较强结合,柔性的开环CB[n]不仅可以在合适的条件下迅速释放客体,还可以设计pH响应的开环CB[n]以达到靶向给药的效果[55]。
Ma等[52]研究了开环CB[n]对紫杉醇等10种不同分子尺寸、含有不同数量碱性氮原子的难溶性药物的增溶效果。结果显示,所有10种药物的溶解度均大幅度提高(23~2750倍),更大的分子空腔使开环CB[n]拥有比HP-β-CD更卓越的增溶效果。开环CB[n]包合抗肿瘤药紫杉醇后使其溶解度增加了2750倍,不仅不影响紫杉醇的体外抗癌活性,而且能更有效地杀灭宫颈癌细胞(HeLa)和卵巢癌细胞(SK-OV-3)。结构属性使开环CB[n]可以优先结合阳离子和芳香族药物,且对中性药物也有良好的增溶效果。
毒理学研究表明,在浓度高达10mmol/L时,开环CB[n]对人肝细胞HEK 293、人肝细胞HepG2、人单核细胞THP-1均显示出低毒性,其中对HepG2的细胞毒性与HP-β-CD相当。原代人红细胞的溶血分析结果显示,开环CB[n]不会显著增加细胞的裂解。体内毒性结果显示,接受最大剂量静脉注射开环CB[n](1230mg/kg)的小鼠疾病与体重变化情况与静脉注射磷酸盐缓冲液相当,证明其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3.3 葫芦[n]脲作为增溶剂的应用前景
CB[n](n=6, 7, 8)的空腔尺寸与α-、β-、γ-CD相当[56],但是刚性结构和缓慢的解离动力学限制了其增溶剂的应用。开环CB[n]由于亲水磺酸基团的修饰使其在水中的溶解度达346mmol/L,空腔直径约为10.74~11.37 Å[52]。CB[n]家族中特有的羰基有利于包合阳离子客体,开环结构能包裹更大的分子,这大大增加了它的应用范围。这些特性赋予了开环CB[n]作为增溶剂的巨大潜力。虽然多项体外细胞毒性测试表明开环CB[n]的细胞毒性较低[57],但是CB[n]若想更深入的应用于药物增溶领域,还需要一系列更为系统全面的毒理学研究。
4. 结语
随着新药开发的日益困难,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溶解度正逐渐成为药物开发的重要方向和突破口之一,因此增溶技术就显得愈发重要,而增溶剂的应用就成为了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大环化合物对药物优异的增溶能力使得其可以作为现有药物增溶剂的有效补充,解决制药工业中遇到的难题。同时,价格低廉、经济易得、方便修饰等优点进一步增加其未来工业应用的潜力。
目前,大环化合物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1)通过包合实现的增溶效果会使可封装药物的大小受到大环化合物的空腔尺寸限制。但是大环化合物的多样性和易修饰性正在逐步丰富客体的种类,新开发的主体如开环CB[n]等既有良好的增溶能力,又有更大的空腔,进一步拓展了大环化合物可增溶药物的范围;(2)基于环糊精作为增溶剂的上市剂型显示出了良好的生物利用度,但因为缺少药物辅料所需的全面毒理学评估,大环芳烃和葫芦脲还未获批准上市,其安全性评价还只停留在实验研究阶段。为了真正的走向生产和应用,还需要进行更为标准、更为全面的安全性评估。
-
-
[1]
Khadka P, Ro J, Kim H, et al. Asian J. Pharm., 2014, 9(6): 304~316.
-
[2]
Loftsson T. Int. J. Pharm. 2017, 531(1): 276~280.
-
[3]
Li P, Tabibi S E, Yalkowsky S H. J. Pharm. Sci., 1999, 88(5): 507~509. doi: 10.1021/js980433o
-
[4]
Li Z, Chen S, Gu Z, et al. Trends Food Sci. Technol., 2014, 35(2): 151~160. doi: 10.1016/j.tifs.2013.11.005
-
[5]
Jambhekar S S, Breen P. Drug Discov. Today, 2016, 21(2): 363~368. doi: 10.1016/j.drudis.2015.11.016
-
[6]
Loftsson T, Brewster M E. J. Pharm. Sci., 1996, 85(10): 1017~1025. doi: 10.1021/js950534b
-
[7]
Crini G. Chem. Rev., 2014, 114(21): 10940~10975. doi: 10.1021/cr500081p
-
[8]
蔡浩峰, 薛可, 卜慧敏, 等. 食品工业科技, 2017, 38(15): 102~106.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GZS201903001.htm
-
[9]
Loftsson T, Duchene D. Int. J. Pharm., 2007, 329(1-2): 1~11. doi: 10.1016/j.ijpharm.2006.10.044
-
[10]
Li Z, Wang M, Wang F, et al. Appl. Microbiol. Biotechnol., 2007, 77(2): 245~255. doi: 10.1007/s00253-007-1166-7
-
[11]
Jansook P, Prajapati M, Pruksakorn P, et al. Int. J. Pharm., 2020, 574: 118896. doi: 10.1016/j.ijpharm.2019.118896
-
[12]
杜瑶, 周树娅, 杨云汉, 等. 分析化学, 2019, 47(3): 371~379.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FJY202001002.htm
-
[13]
Connors K A. Chem. Rev., 1997, 97(5): 1325~1358. doi: 10.1021/cr960371r
-
[14]
Alvi N P, McMahon T T, Devulapally J, et al. J. Cataract Refract. Surg., 1997, 23(6): 849~855. doi: 10.1016/S0886-3350(97)80242-8
-
[15]
Stella V J, Rajewski R A. Int. J. Pharm., 2020, 583: 119396. doi: 10.1016/j.ijpharm.2020.119396
-
[16]
Yan V C, Muller F L.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20, 64(12): e01920-20.
-
[17]
Sahakijpijarn S, Moon C, Koleng J J, et al. Pharmaceutics, 2020, 12(11): 1002. doi: 10.3390/pharmaceutics12111002
-
[18]
Miller R D. Anesth. Analg., 2007, 104(3): 477~478. doi: 10.1213/01.ane.0000255645.64583.e8
-
[19]
Fenyvesi E, Szeman J, Csabai K, et al. J. Pharm. Sci., 2014, 103(5): 1443~1452. doi: 10.1002/jps.23917
-
[20]
Saokham P, Loftsson T. Int. J. Pharm., 2017, 516(1-2): 278~292. doi: 10.1016/j.ijpharm.2016.10.062
-
[21]
Tsai Y, Tsai H H, Wu C P, et al. Food Chem., 2010, 120(3): 837~841. doi: 10.1016/j.foodchem.2009.11.024
-
[22]
Ol'khovich M, Sharapova A, Blokhina S, et al. J. Mol. Liq., 2019, 273: 653~662. doi: 10.1016/j.molliq.2018.10.053
-
[23]
Yang Z, Argenziano M, Salamone P, et al. J. Incl. Phenom. Macrocycl. Chem., 2016, 86(3-4): 263~271. doi: 10.1007/s10847-016-0657-5
-
[24]
Morrison P W, Connon C J, Khutoryanskiy V V. Mol. Pharm., 2013, 10(2): 756~762. doi: 10.1021/mp3005963
-
[25]
Stella V J, He Q. Toxicol. Pathol., 2008, 36(1): 30~42. doi: 10.1177/0192623307310945
-
[26]
Ortolan A O, Øestrøm I, Caramori G F, et al. Organometallics, 2018, 37(13): 2167~2176. doi: 10.1021/acs.organomet.8b00292
-
[27]
Lo P K, Wong M S. Sensors (Basel), 2008, 8(9): 5313~5335. doi: 10.3390/s8095313
-
[28]
Ukhatskaya E V, Kurkov S V, Matthews S E, et al. J. Incl. Phenom. Macrocycl. Chem., 2013, 79(1-2): 47~55.
-
[29]
Yang W, de Villiers M M. Eur. J. Pharm. Biopharm., 2004, 58(3): 629~636. doi: 10.1016/j.ejpb.2004.04.010
-
[30]
Bayrakci M, Ertul ş, Yilmaz M, J. Chem. Eng. Data, 2011, 57(1): 233~239.
-
[31]
Xue M, Yang Y, Chi X, et al. Acc. Chem. Res., 2012, 45(8): 1294~1308. doi: 10.1021/ar2003418
-
[32]
Ogoshi T, Ueshima N, Yamagishi T A, et al. Chem. Commun., 2012, 48(29): 3536~3538. doi: 10.1039/c2cc30589e
-
[33]
Yakimova L S, Shurpik D N, Gilmanova L H, et al. Org. Biomol. Chem., 2016, 14(18): 4233~4238. doi: 10.1039/C6OB00539J
-
[34]
Zhang H, Liu Z, Fu H. Nanomaterials (Basel). 2020, 10(4): 651.
-
[35]
Bahojb Noruzi E, Molaparast M, Zarei M, et al. Eur. J. Med. Chem., 2020, 190: 112121. doi: 10.1016/j.ejmech.2020.112121
-
[36]
Yang W, de Villiers M M. AAPS J., 2005, 7(1): E241~248.
-
[37]
Ukhatskaya E V, Kurkov S V, Matthews S E, et al. J. Pharm. Sci., 2013, 102(10): 3485~3512. doi: 10.1002/jps.23681
-
[38]
Hart P D, Armstrong J A, Brodaty E. Infect. Immun., 1996, 64(4): 1491~1493. doi: 10.1128/iai.64.4.1491-1493.1996
-
[39]
Liu Y, Chen X, Ding J, et al. ACS Omega, 2017, 2(8): 5283~5288. doi: 10.1021/acsomega.7b01032
-
[40]
Shangguan L, Chen Q, Shi B, et al. Chem. Commun., 2017, 53(70): 9749~9752. doi: 10.1039/C7CC05305C
-
[41]
Yu G, Yu W, Mao Z, et al. Small, 2015, 11(8): 919~925. doi: 10.1002/smll.201402236
-
[42]
Espanol E S, Villamil M M. Biomolecules, 2019, 9(3): 90. doi: 10.3390/biom9030090
-
[43]
Pan Y C, Hu X Y, Guo D S. Angew. Chem. Int. Ed., 2021, 60(6): 2768~2794. doi: 10.1002/anie.201916380
-
[44]
Cao L, Hettiarachchi G, Briken V,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46): 12033~12037. doi: 10.1002/anie.201305061
-
[45]
Olea Ulloa C, Ponce-Vargas M, Munoz-Castro A. Phys. Chem. Chem. Phys., 2018, 20(46): 29325~29332. doi: 10.1039/C8CP04936J
-
[46]
Xue W, Zavalij P Y, Isaacs L. Org. Biomol. Chem., 2019, 17(22): 5561~5569. doi: 10.1039/C9OB00906J
-
[47]
Lee J W, Samal S, Selvapalam N, et al. Acc. Chem. Res., 2003, 36(8): 621~630. doi: 10.1021/ar020254k
-
[48]
Uzunova V D, Cullinane C, Brix K, et al. Org. Biomol. Chem., 2010, 8(9): 2037~2042. doi: 10.1039/b925555a
-
[49]
Chen J, Liu Y, Mao D, et al. Chem. Commun., 2017, 53(62): 8739~8742. doi: 10.1039/C7CC04535B
-
[50]
Liu S, Ruspic C, Mukhopadhyay P, et al. J. Am. Chem. Soc., 2005, 127(45): 15959~15967. doi: 10.1021/ja055013x
-
[51]
Yang X, Zhao W, Wang Z, et al. Food Chem. Toxicol., 2017, 108(Pt B): 510~518.
-
[52]
Ma D, Hettiarachchi G, Nguyen D, et al. Nat. Chem., 2012, 4(6): 503~510. doi: 10.1038/nchem.1326
-
[53]
Li S, Chan J Y, Li Y, et al. Org. Biomol. Chem., 2016, 14(31): 7563~7569. doi: 10.1039/C6OB01060A
-
[54]
Ahmadian N, Mehrnejad F, Amininasab M, J. Chem. Inf. Model., 2020, 60(3): 1791~1803. doi: 10.1021/acs.jcim.9b01087
-
[55]
Li F, Liu D, Liao X, et al. Bioorg. Med. Chem., 2019, 27(3): 525~532. doi: 10.1016/j.bmc.2018.12.035
-
[56]
Robinson E L, Zavalij P Y, Isaacs L. Supramol. Chem., 2015, 27(5-6): 288~297. doi: 10.1080/10610278.2014.940952
-
[57]
Sigwalt D, Moncelet D, Falcinelli S, et al. ChemMedChem, 2016, 11(9): 980~989. doi: 10.1002/cmdc.201600090
-
[1]
-
图 3 典型柱[n]芳烃的结构和模型[34] (n=5~10)
Figure 3 Structural and cartoon representations of typical pillar[n]arenes (n=5~10)
表 1 25℃下CDs(α-,β-,γ-CD)的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CDs (α-, β-, and γ-) at 25℃
α-CD β-CD γ-CD 空腔直径/Å 4.7~5.3 6~6.6 7.5~8.3 空腔体积/Å3 100 160 250 腔内水分子数 2.5 5.0 8.5 水中溶解度/(mol/L) 0.12 0.016 0.17 溶解吉布斯自由能/(kJ/mol) 15 20 14 -

 扫一扫看文章
扫一扫看文章
计量
- PDF下载量: 44
- 文章访问数: 6238
- HTML全文浏览量: 1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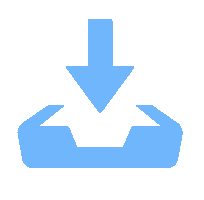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