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ation: He Juan. The Chinese Nomenclature for the Heterocyclic Compounds since 1932[J]. Chemistry, 2019, 82(4): 373-378.

1932年以来杂环化合物的中文命名
English
The Chinese Nomenclature for the Heterocyclic Compounds since 1932
-
Key words:
- Heterocycle
- / Nomenclature
- / Free translation
- / Transliteration
- / Terms
-
中文化学名词自193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化学命名原则》之后,终于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局面,有了统一的标准。该原则对于杂环化合物的命名非常简略,除采用“两个从口旁之字”[1]的音译名作为杂环母核的简名外,对系统名称简单规定:“杂环从构成环核各元素之数,称为若干某若干某圜。碳以外如有二种元素时,从氧、硫、氮之顺序,而略碳字”[1]。如呋喃的系统名称为一氧二烯伍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学术名词工作十分重视。1950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就化学名词而言,杂环母核的命名,成为“化学物质命名中最困难而亟待解决的问题”[2]。化学家们纷纷发表提议。不少人对音译口旁名称非常不满。他们倡议创制一些表意的汉字来指称杂环母体,再缀上杂原子的名称,作为杂环化合物的系统名称。
同时期颁布的1950年、1953年和1960年《原则》,在杂环母核的系统名称上,虽然都接纳了这一意译的用字取向,但对于口旁简名并没有废除。1980年《原则》否弃了此前的意译杂环名称,重新确立了口旁音译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1932年以后,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杂环母核的命名吸引了不少化学家的注意。但他们提议的各种意译杂环名词最终并没有得到采纳,而他们颇为反对的在1932年《原则》中提出的呋喃等音译名称终得以沿用。这是中文化学名词历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主要通过考察1932年以来杂环化合物的命名情况,并结合历史背景,对该现象进行剖析,进而对化学物质命名用字中的音译与意译提出一些思考。
1. 1932年以来杂环化合物命名演变
1932年以来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2年《原则》颁布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80年《原则》颁布为第二阶段。1980年《原则》颁布以后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命名特点是命名原则非常简略,以音译口旁名称作为简名。该时期的代表方案是1932年《原则》。1937年和1945年,分别出版了1932年《原则》的修订本和增订本,改动不大。在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原则上,几乎没有变更。
如1945年《原则》规定:“杂环从构成环核各元素之数,称为若干某若干某圜。碳以外如有二种元素时,从氧、硫、氮之顺序,而略碳字。但主要之母核,得特创两个或两个以上从口旁之字,以为简名”[3]。以及“繁复之骈合杂圜,除用系统名外,亦得从其原名之音,特创两个或两个以上从口旁之字,以为简名;或从其来源,或用旧有名词,以作其简名”[3]。这些陈述除个别措辞有删减和变更外,主要的变动是把“两个从口旁之字”的规定改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从口旁之字”。
在命名一些复杂的杂环化合物时,1932年和1945年《原则》在实际应用中遇到了困难。一些化学家提出了改革方案。比如,裘家奎先生就新造畉、









第二阶段的主要命名特点是,化学家们拟订了各式各样表意的新字用于杂环母核的命名,这一意译用字取向也为该时期颁布的几次《原则》所接纳。化学家提出的代表性方案有1949年薛德炯的《有机化学杂环族碳化物命名原则革新刍议》和1951年黄新民的《关于杂环化合物命名的意见》。杜作栋、马太和等参与了讨论。
其中,薛德炯的部分提议直接为1950年《原则》采用:“杂环族化合物的系统名称,过去所用者,过嫌笨拙,今采薛德炯先生的建议,加以简化”[5]。黄新民则是负责起草1950年《原则》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查小组的五位委员之一,其余四位是吴承洛、张江树、张龙翔、曾昭抡[5]。1951年12月19日,该小组曾召集化学物质名词编订座谈会,黄新民和陶坤被推举负责研究杂环母核的命名问题,并要求在1953年2月的全国性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前提出报告[2]。1952年6月,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查小组更名为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并增聘了杨葆昌和邢其毅两位委员[2]。1953年座谈会之后,编订了1953年《原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1953年《原则》也不敷使用。1956年,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对1953年《原则》进行修订,草拟了《有机化合物的系统命名原则和俗名命名总则草案》,送往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后于1958年7月经过庄长恭、杨葆昌、邢其毅、黄新民、张滂等化学家的审阅,又几经征求意见、讨论和修订,最后编成1960年《原则》[6]。
第三阶段的代表性方案为1980年《原则》。该原则是1960年《原则》的增修订本,由中国化学会推荐使用,参加起草和修订工作的化学家有王序、邢其毅、王葆仁、张滂等。1980年《原则》对于基本杂环母核名称,废弃了1960年《原则》中的氧茂、硫芑等意译名,沿袭了1932年《原则》中的口旁名称;这在如下陈述中表达得很清楚:“原则上是2~3个汉字的音译,这与环烃中已通用的‘苯’、‘萘’、‘蒽’、‘菲’……的名称具有类似的普遍性,名词的结构尊重我国习惯,以‘口’旁作为杂环的标志”[7]。
为了论述方便,把1932年以来主要的杂环化合物命名情况列于表 1。
表 1

2. 几点分析
从表 1可更为清楚地看出杂环母核的命名在三个不同时段的特点。下面将结合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命名方案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和分析。
2.1 新中国初期化合物命名用字的“会意”原则
我们现今所使用的中文化学名词中,有许多最基本的词汇都是采用音译法来命名的。譬如,构成无机化合物名称的基本词汇——元素名称,绝大多数都是用单字音译法拟定的。构成有机化合物名称的基本词汇,如芳香母核的苯、萘、蒽、菲,和杂环母核的呋喃、噻吩、吡咯等,也是用音译法命名的。“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以音译为主的命名原则,源自1932年《原则》中的规定:“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1]。
新中国成立以后,化学名词的审订和统一工作随即提上议程。在化合物的命名用字上,1950年编订的《原则》对1932年《原则》作出了重大修订,规定:“对于化合物的名称,在必要用新字时,倾向于采用会意与象形之原则,不像以前之太偏重译音”[5]。1953年《原则》规定:“化合物定名用字,以会意为主,谐声、象形次之”[2]。“会意”原则在杂环母核的命名用字“


具体来讲,1950年《原则》规定:“杂环族母核所含的原子数,以叁、肆、伍、陸等字表示,再加圜字于其后,加杂原子名称于其前以命名。具有芳香性质的伍、陸杂环化合物,特创新字‘




“会意”原则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它与新中国文教方针的方向有关。1950年《原则》前附郭沫若所作序文,对新中国成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工作时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有明确交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达到了空前的巩固与统一。共同纲领对于国家各项建设工作都规定了明确的政策方针。一年以来,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根据了这些政策方针,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查、统一与改革。这是伟大的国家改造工程。学术工作自然也是整个国家改造工作中的一环。共同纲领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教育、卫生、艺术科学既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中国学术界在思想上便获得共同的准绳,因而对于旧的学术文化才可能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统一学术名词的要求,正是适应这新的情况,作为改革学术工作之一而被提出来的[5]。
对于《共同纲领》在文化政策上的特点,周恩来1949年9月20日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中概括的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问题……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8]。
化学家黄新民在提出杂环化合物的命名方案之前,先谈及新中国文化政策的这一特点:
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之后,文化上也要翻身;这里边就包括着科学的独立,或者说:要求一套民族的、大众的科学;因此客观上有统一学术名词的必要[9]。
“一个名词或一套制度,必须经过实践,在课堂上,在工厂里大家应用,大家考验以后,才能看出它的优劣来的,才可以提高到更正确的地步”[9]。他接着说,“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原则,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9]。杂环化合物的命名必须改革,因为“现在的命名正确与否实在是大大的关联着今后科学的发展”[9]。
1933年的化学命名原则……把

否定了“呋喃”等谐声的命名方式后,黄新民提出了一套意译的杂环命名方案。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特创意译字


这套方案得到“学术名词统一委员会化学组曾昭抡,吴承洛,张龙翔,陶坤四先生,清华大学冯新德先生,北京大学王序,何端僧先生,燕京大学张滂先生,华大工学院王凡先生”的“启示或赞同”[10],“北大药学系三四年级同学和清华化学系四年级同学”[10]给出了意见。可见,采用意译方法命名杂环化合物,在新中国初期为大多数化学家所认可。
2.2 对音译杂环名称的态度
从表 1可见,民国后期,裘家奎拟制的杂环化合物命名方案仍然以音译为基础。新中国初期,对杂环母核的命名用字采用意译方法,成了主流意见。该时期颁布的1950年、1953年和1960年《原则》也采纳了意译用字,但并没有废除音译口旁名称。三个《原则》对音译简名分别持“宜少用”、“暂予保留”及认可的态度。具体陈述如下:
1950年《原则》:“主要的杂环母核,得从其英文名之音,创两个口旁的字作为简名。所造口旁之字均从字之右半部读音。但此种方法宜少用”[2]。
1953年《原则》:“杂环母核用下述方法来系统地命名。以往用造口旁字的命名法,有欠系统,但其已沿用者,可暂予保留并用”[2]。
1960年《原则》:“在制订简名时,可以根据目前沿用的习惯分别用‘噁’、‘噻’、‘吖’来表示氧杂、硫杂和氮杂,用‘砒’表示砷杂”[6]。这是明显支持将音译字用于简名的制订。在该《原则》所列重要杂环的特定名称中,音译简名都是置于系统名之前。如

同时期的化学家,大多数同意,“新创口旁字的难记,人人皆有同感,所以必须改良”[11]。然而,在命名复杂的杂环化合物时,“母核的名称太长……在印刷、笔记、讲解时都反乎节省的原则,容易遭到反对”[9],而音译名较系统名具有简短、易读等明显优势,很有存在的必要。
如农业化学家马太和认为,“命名应采用系统名……不赞成音译,因各国文字发音不同,我国南北各地发音也不同,音译会造成混乱”,但“复杂的化合物,读系统名不方便或麻烦时,也可音译,但应该简单,照顾实际应用”[12]。化学家顾翼东认为:“系统名和音译应兼顾。如嘌呤、呋喃、嘧啶等名,仍可沿用。例如二氮杂苯,必须说明1,3-二氮杂苯或间二氮杂苯,则不如译‘嘧啶’,一听便知……总之系统名太长,太易混,用得多者宜译音。另一方面结构式未曾确定,或提炼初步所得的化合物,无法意译时,只能音译”[12]。
化学家黄新民虽然历陈谐音造字的缺点,但也无奈地表示必要时候还得使用这种命名方法:“根据已造的字看来,实在容易混淆,引人入迷途。例如吡咯(Pyrrole)与吡啶(Pyridine)同用一吡字,二者却又没有可以由吡字表示出来的关系,这起①不是大大的违反命名的总则吗?……因此,在这次审定的命名原则中,对于简单的杂环就废除了这种造字的办法。可是对于复杂的杂环仍不得不保留此法”[9]。
① “起”字应该是“岂”字的误写。
薛德炯“不满于”口旁简名“已十余年”[13],认为它们“像佛经中的‘唵嘛呢叭咪吽’简直莫名其妙”[12]!如若用口旁音译字来命名dithiadiazole等杂环化合物,“势必噁噁噻噻,唑唑嗪嗪,满纸咿哑,一若番书,虽有谪仙李太白其人,恐亦难于索解。此口旁之简名所以不能不革除(割爱)也”[13]。即便如此深恶痛绝口旁名称,也承认,“稠杂圜之结构,繁复者多,故其系统名,类多冗长。为便于名举计,确有特定简名之必要”[13]。不过他建议“从原名之音,特创口旁字之简名,至少须于名末多加一个足以表示其主要官能之字”[13]。如咖啡宜命名为“咖啡鹼”。
2.3 意译杂环名词的特点分析
表 1反映了1932年以来杂环母核命名所采纳的主要意译字。代表用字有









在黄新民的方案中,同样的






黄新民所创造的




在黄新民方案中,杂环化合物的名称,是“在与它构造相当的芳香族化合物之名称前加上杂原子的名称”[9]得来。如呋喃称氧







马太和创制





如果不创造新字,那么可以使用“杂”字来表示杂原子的特殊性。但杂字是置于杂原子的名称之前还是之后,各方案又不一样。如1953年座谈会把吡啶命名为杂氮苯[2],而1953年和1960年《原则》则命名为氮(杂)苯①。
① 1953年和1960年《原则》都规定,杂字在不致误会的情况下可以略去。因此,这里在氮(杂)苯的名称中加了个括号,表示可以省略。
从上述讨论可看出,采用意译方法来命名杂环母核,在三个层面上出现分歧。一是对于不饱和或芳香杂环母体的翻译,是采用口旁或是草字头,以及是用汉文数字还是天干来表示杂环中的原子个数,因人而异。而且,对于五元环和六元环的处理,有时也并不遵循同一命名思路。二是对于杂原子的翻译,有的认为仅仅翻译杂原子的名称即可;有的认为要创造新字来指称杂原子,以区别于非杂环中的原子;有的建议把杂字置于杂原子的名称之前,有的则建议置后。三是杂原子的译名,是放在杂环母核名称之前还是之后,也有分歧。
3. 余论
自19世纪中叶西方化学传入中国以来,有机物的中文命名一直就是个棘手的问题。把西文有机物名称用汉字完全音译过来是当时的普遍做法,这样的名称繁冗至极,没有意义,难以记诵,让人苦不堪言。1908年,虞和钦于《有机化学命名草》中提出第一个系统的有机物中文命名方案,其特点是不创造新字,且以意译为基础。意译不仅表现在整个有机物的中文名称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机物的类名也是意译的。后续有机物命名方案大多深受虞和钦命名理念的影响,在有机物的类名用字上采取了意译字或象形字,较少用到音译字[15]。这在1932年以前芳香族母核和杂环母核的名称制订上表现特别突出。
然而,在芳香母核和杂环母核的命名用字上,1932年《原则》摒弃了此前的以意译或象形为主的各种旧译名,创制了全新的苯、呋喃等音译名称。如此之“标新立异”应该并不是有意为之,因为1932年《原则》在定名总则中还明确提出“旧有译名,可用者,尽量采用”[1]。之所以以“革命手段处置”[16]历史译名,恐怕更多地因为,当时制定化学名词的化学家共同体切身体会到在化合物命名用字时采用音译较意译或象形更为合理。其合理性在于,用汉字译出西文名称的首音或次音或尾音这个音译标准容易操作和达成统一;而意译或象形的标准不仅视化学家个人表现出差异,还常常因化学物质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也极难达成共识[17]。
可是,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寻找合适的意译字用于中文化学命名,总是天然地为国人所喜爱。新中国初期,受当时文教方针的影响,化合物命名用字的“意译”原则又被重新提倡。历史似乎总在重演。新中国的化学家们已然忘却了1932年《原则》处理杂环母核历史意译名的经验和“革命”做法,他们也像前辈一样热衷于在杂环母核的命名上提出各种基于意译字的方案。准确地说,在命名化学物质时,如果对于意译的“意”能达成一致,那么意译用字确实比音译字占有优势。中文化学名词烷、烯、炔便是如此。在烷、烯、炔的命名历史上,由于化学家们翻译的“意”高度统一,即分别译出碳碳单键、碳碳双键、碳碳叁键的饱和、不饱和与更不饱和之“意”,从而,音译名较意译名具有标准统一的优势便不再凸显,因此,最终是意译名胜出[18]。
不过,杂环母核的命名要复杂得多。杂环化合物的命名与其对应的脂环或芳环化合物的命名密切相关。对杂环母核进行意译,不仅要翻译对应的脂环或芳环母体,还要翻译杂原子的名称,并且二者先后顺序的安置也要协商一致,因此,较用意译方法翻译烷、烯、炔来说,杂环母核的意译产生分歧的层面更多。
相比之下,呋喃等音译名,虽然有“与实际毫无联系”与“难记”等缺点,但也较系统长名简短、方便,具有“省手续”[16]等优点。所以,即便是薛德炯和黄新民这样对口旁音译简名非常不满的化学家,也认为在特殊情况下有保留或改进音译名的必要。这也是1950年、1953年和1963年《原则》对口旁简名的态度由“宜少用”逐渐过渡到“认可”的原因。1980年《原则》重新启用呋喃等音译名,更是证明了1932年《原则》确立化学物质命名用字音译原则的合理性和当时化学家群体决策之颇具远见。
-
-
[1]
国立编译馆.化学命名原则.南京: 国立编译馆, 1933: 95;1.
-
[2]
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 3,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4: 106;123;修订本的补充说明; 1;127;108.
-
[3]
国立编译馆.化学命名原则(增订本). 4, 上海: 正中书局, 1947: 99;102.
-
[4]
裘家奎.科学, 1947, 29(2): 50.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1985-HJXX198503006.htm
-
[5]
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1: 前记, ii; 前记, i; 102;序, i~ii.
-
[6]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3次印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5: 1369;1386;1388.
-
[7]
中国化学会.有机化学命名原则.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3: 43.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19.
-
[9]
黄新民.化学, 1951, 13(1): 25~31. http://www.cqvip.com/Main/Detail.aspx?id=26382140
-
[10]
黄新民.化学, 1951, 13(2): 83~85. http://www.cqvip.com/qk/93924A/200402/9770167.html
-
[11]
杜作栋.化学, 1951, 13(4): 194.
-
[12]
化学通报, 1953, 16(12): 551~556.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XTB200507013.htm
-
[13]
薛德炯.科学, 1949, 31(8): 230~235.
-
[14]
马太和.化学, 1952, 14(2): 20.
-
[15]
何涓.自然科学史研究, 2014, 33(4): 491. http://www.cqvip.com/QK/90972X/201404/664103003.html
-
[16]
国立编译馆.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专刊.南京: 国立编译馆, 1932: 92;222.
-
[17]
何涓.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3, 34(4): 460~472. http://www.cqvip.com/QK/91361X/201304/48094969.html
-
[18]
何涓.化学通报, 2016, 79(7): 670.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xtb2201607015.aspx
-
[1]
-
表 1 1932年以来主要杂环母核的中文名称
Table 1. The Chinese terms for basic heterocyclic nuclei since 1932

-

 扫一扫看文章
扫一扫看文章
计量
- PDF下载量: 36
- 文章访问数: 2893
- HTML全文浏览量: 7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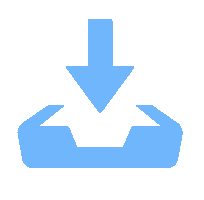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