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ation: Xie Yanyan, Chai Yun, Zhang Puyu. Study on Dissolving Cellulose by Ionic Liquids[J]. Chemistry, 2020, 83(12): 1104-1112.

离子液体溶解纤维素的研究
English
Study on Dissolving Cellulose by Ionic Liquids
-
Key words:
- Cellulose
- / Ionic liquids
- / Dissolution
- / Recovery
-
随着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石油、煤等化石类资源日渐枯竭,利用天然的高分子材料来代替石油基资源迫在眉睫。纤维素是自然界最丰富的可再生聚合物之一[1, 2],来源丰富,主要存在于木材、棉花、麻、竹、甘蔗渣等植物中。每年,自然界产生的纤维素量超过千亿吨[3],是取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因此,将可生物降解的纤维素再生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商业生物材料具有重要的应用意义。然而,目前每年真正得到利用的纤维素只有7%[4],众所周知,纤维素水解是进行下游工艺之前的关键步骤。然而,因为它的高度结晶结构和纤维之间广泛的分子间和分子内氢键网络,导致纤维素不溶于水和大多数普通溶剂[5]。纤维素是由D-葡萄糖基以β-1, 4苷键连接形成的链状高分子化合物,分子中包含大量的分子内及分子间氢键(图式 1),由于不同的纤维素链的排列方式差别较大[6],因而形成了无定形区和结晶区,由于结晶区的存在使其难溶于一般的有机溶剂。
图式 1
为了解决纤维素加工的难题,人们开发了多种溶剂体系,包括黏胶溶剂和铜氨溶液,N-甲基吗啉-N-氧化物(NMMO)[7, 8],氯化锂/甲基乙酰胺、硫氰酸铵/液氨、多聚甲醛/二甲基亚砜等。但这些传统溶剂体系存在溶液不稳定、毒性大、污染环境、回收困难、溶解过程复杂、产品性能差、相关成本高(NMMO合成的条件比较苛刻,成本较高,必须使其回收率高于99.5%才有经济效益[9])等缺点。2004年,张俐娜等[10]开发了纤维素的新一类溶剂(氢氧化钠/尿素、氢氧化钠/硫、氢氧化钠/尿素水溶液)体系,采用7(wt)%氢氧化钠/12(wt)%尿素水溶液预冷至-12℃,它能迅速溶解(5min内完全溶解)纤维素得到透明的溶液,这种溶解方法价格低廉、生产周期短,在国际上开辟了绿色制备纤维素溶液的新方法[11]。但是,其溶解纤维素的条件苛刻,且溶解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物纤维素氨基甲酸酯,这些局限性阻碍了它们的实际应用,促使我们开发新的溶剂体系。
离子液体(ILs)是指由有机阳离子和无机或有机阴离子组成的,在室温或近室温下呈液态的熔融盐。ILs拥有独特的优良性质,如蒸汽压低、不挥发、不可燃、热熔大、热稳定性好、离子电导率高、电化学窗口宽、溶解能力强等,因此ILs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溶剂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此外,ILs具有很好的可调控性,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阴离子或调节阳离子的结构,获得结构丰富、功能多样的ILs,因此被认为是“绿色可设计的溶剂”。
图 1是2001~2020年学者发表的以ILs作为溶剂溶解纤维素的相关论文数据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从2005年开始,每年发表的文章量逐年增加,其中2016、2017年发文量最多,超过260篇/年,引文频次(图 2)也是逐年增多,2019年已经达到13000次。利用ILs作为纤维素的溶剂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很多学者做了相关工作,现综述如下。
图 1
图 2
1. 不同种类ILs溶解纤维素的研究
1.1 基于咪唑类阳离子的ILs
到目前为止,用于纤维素溶解的ILs中,最常用且效果最好的就是烷基咪唑鎓类ILs[5]。本文介绍几种阳离子为咪唑类而阴离子不同的ILs对纤维素的溶解性能。
1.1.1 阴离子为卤素类的ILs
早在1934年,Graenacher[12]就发现熔融的氯盐化N-乙基吡啶鎓能够溶解纤维素,并能用来制备一些纤维素衍生物,但是,由于当时离子液体的概念还没有被提出,人们对这类物质的性能还缺乏认识,在当时被认为几乎没有实际价值[13]。直到2002年Swatloski等[14]首次报道了氯化1-丁基-3-甲基咪唑鎓([BMIM]Cl)可以很好地溶解纤维素,在纤维素的溶解方面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继Swatloski之后,2003年,任强等[15]以N-甲基咪唑、烯丙基氯和氯丁烷为原料合成了氯化1-烯丙基-3-甲基咪唑鎓[AMIM]Cl(结构如图式 2(a)所示),并发现其对纤维素具有较好的溶解性能。通过和[BMIM]Cl(结构如图式 2(b)所示)进行对比发现,当温度范围为90~100 ℃、浓度范围为3(wt)%~5(wt)%、磁力搅拌作用下,两种ILs均能将纤维素完全溶解,但[AMIM]Cl对纤维素的溶解速率明显优于后者,在较短时间即出现溶胀、溶解。
图式 2
2005年,罗慧谋等[16]合成了一种新型含羟基的功能化ILs——氯化1-(2-羟乙基)-3-甲基咪唑鎓[HOEtMIM]Cl (如图式 3所示),发现阳离子咪唑鎓上含有羟基的ILs是溶解纤维素的良好溶剂,因为它与纤维素形成了氢键。温度为70℃时,微晶纤维素(MCC)在[HOEtMIM]Cl中的溶解度可达5(wt)%~7(wt)%。而且,在相同的溶解条件下,[HOEtMIM]Cl对纤维素的溶解性能优于[BMIM]Cl和[AMIM]Cl。主要溶解过程为:将加有一定量ILs的圆底烧瓶加热至70℃,在磁力搅拌下逐份加入活化(用氢氧化钠处理)的纤维素,直到所加纤维素不再溶解,然后将体系冷却至室温,用高速离心机将未溶解纤维素分离出来,即可得到透明的纤维素-ILs溶液。
图式 3
溶解后的纤维素可在水或乙醇凝固浴中控制形态后再生,制备出纤维素纤维(干喷湿纺法)、薄膜和凝胶等材料。相比于从NMMO中得到的再生纤维(Lyocell),ILs纺出的再生纤维素纤维(Ioncell)的韧性略高,拉伸强度和延伸性能都更加理想[17]。
1.1.2 阴离子为磷酸类的ILs
近年来,烷基磷酸酯基ILs已经形成了具有商业吸引力的纤维素溶剂,因为这些ILs可以通过烷基咪唑与相应磷酸酯的一步季铵化反应合成,而且,烷基磷酸酯基ILs的熔点和粘度比其他类型的更低[5]。
2019年,李晓严等[18]采用1, 3-二甲基咪唑磷酸二甲酯[MMIM]DMP对纤维素进行溶解。其溶解过程为:取适量的[MMIM]DMP加入一定量的纤维素加热到110℃,放入2L真空容器中以20r/min的转速在0.007MPa下搅拌90min得到12(wt)%的纤维素衍生物溶液。纤维素在不同温度下完全溶解所需时间见表 1。从表中可以看出,纤维素在ILs中的溶解时间随温度的升高而逐渐减短,说明升高温度有利于纤维素在[MMIM] DMP中的溶解,可能是[MMIM]DMP中的成分可以使纤维素中化学键断裂,而温度的升高可以使[MMIM]DMP中的有效成分活性增加,从而降低了纤维素在ILs中完全溶解需要的时间。
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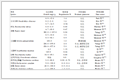 表 1 纤维素在[MMIM]+[MMP]-中完全溶解所需温度和时间Table 1. The temperature and time of cellulose completely dissolved in [MMIM]+[MMP]-
表 1 纤维素在[MMIM]+[MMP]-中完全溶解所需温度和时间Table 1. The temperature and time of cellulose completely dissolved in [MMIM]+[MMP]-温度/℃ 70 80 90 100 110 120 时间/min 160 128 120 108 97 75 Zhao等[19]将干棉麻浆按4%(纤维素浆与ILs)的质量比分别加入含[MMIM]DMP和1-乙基-3-甲基咪唑磷酸二乙酯([EMIM]DEP)的烧瓶中。在70、80、90、100、110和120 ℃的油浴中连续搅拌纤维素溶液,至完全溶解,记录溶解时间(如表 2a、2b所示)。由于棉麻浆结晶度高,用偏光显微镜观察了纤维素的直接溶解过程。当显微镜视野完全变黑时,棉麻浆被认为完全溶解。最终得到了聚合物浓度为4%左右的透明纤维素溶液。
表 2a
溶解温度/℃ 70 80 90 100 110 120 溶解时间/min 400 320 300 270 243 188 表 2b
溶解温度/℃ 70 80 90 100 110 120 溶解时间/min 100 20 11 6 4 2 Hokayem等[20]采用两种不同的膦酸盐基ILs(1, 3-二甲基咪唑甲基膦酸酯[DIMIM] (MeO)(H)PO2和1-乙基-3-甲基咪唑甲基膦酸酯[EMIM](MeO)(H)PO2)溶解棉纤维。通过偏光显微镜观察到在不同溶解时间下,单个棉纤维在[DIMIM](MeO)(H)PO2中的溶解情况:在试验开始后的几十秒内,溶解变得明显,并在2min内完全溶解。这表明,即使在低于100℃的温度下,[DIMIM](MeO)(H)PO2也具有很高的溶解纤维素的能力。
1.1.3 阴离子为羧酸根的ILs
随着对ILs溶解纤维素的深入研究,有相关学者发现乙酸类ILs可更高效地溶解纤维素。羧酸盐型ILs的粘度小于氯化物型ILs,熔点始终低于0℃,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纤维素溶剂之一[5]。Nguyen等[21]用乙酸1-乙基-3-甲基咪唑鎓([EMIM]OAc)为溶剂,可溶解5.5(wt)%~6.5(wt)%的杂杨树生物质,这种方法为木质素-纤维素丝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并且减少了前期对纤维素进行纯化提取的步骤,降低了生产成本。Isik等[22]在加热条件下利用[EMIM]OAc可溶解16(wt)%的纤维素,而通过微波加热可溶解25(wt)%的纤维素。
Liu等[23]发现,ILs的氢键碱度(β)对纤维素的溶解性有很大影响。根据Kamlet-Taft参数,乙酸1-丁基-3-甲基咪唑鎓[BMIM]OAc(β=1.09)的氢键碱度比[BMIM]Cl(β=0.83)更强,有利于纤维素聚合物链氢键网络的弱化,加快纤维素的溶解。
1.1.4 阴离子为其他官能团的ILs
Lethesh等[24]制备了具有非常规有机阴离子的碱性ILs—酚酸酯离子液体,并用于纤维素的溶解研究。在室温下,将高浓度的纤维素溶解在酚基咪唑[C2MIM]OPh中,并与有机溶剂结合,在100℃下,纤维素溶解率高达45(wt)%。
Grossereid等[25]合成了具有非常规阴离子的新型双官能化N-氧乙烯-N-磺丙基咪唑基ILs,并研究这种新型IL混合二甲基甲酰胺(DMF)溶解MCC纤维素的能力,结果表明,这种新型IL能成功溶解纤维素。
1.2 阳离子为其他类ILs
除咪唑类ILs对纤维素有良好的溶解性外,Sixta等[26]发现1, 5-二氮杂双环[4.3.0]-5-壬烯乙酸盐([DBNH]OAc)可有效溶解纤维素。2015年,Raut等[27]发现一种吗啉类ILs N-烯丙基-N-甲基吗啉乙酸酯([AMMorp]OAc)能有效溶解纤维素,当温度为120℃时,这种IL能在20min内溶解质量分数为30%的纤维素,并且其毒性更低和更稳定。
King等[28]研究了新一代ILs的结构,其基础是有机超碱1, 1, 3, 3-四甲基胍(TMG)与甲酸、乙酸和丙酸等羧酸的共轭。这种方法产生的ILs既能快速溶解纤维素到高浓度,又可通过蒸馏回收,回收率和纯度超过99%。
付林林等[29]采用一步法合成氯化N-烯丙基吡啶鎓([APyr]Cl),研究了其对纤维素的溶解性能,结果表明,[APyr]Cl为纤维素的优良溶剂。随着温度的升高,[APyr]Cl对棉浆粕(DP=556)的溶解速率提高,溶解度增大(在120℃下,溶解度达到19.71%),再生纤维素的聚合度(DP)逐步降低。同时,他们还研究了不同聚合度的纤维素在此温度下的溶解度,发现脱脂棉纤维素(DP=1971)的溶解度可达15.29%(如表 3所示)。
表 3
溶解温度/℃ 溶解时间/min 溶解度/% 再生纤维素的DP 115 36 14.72 256 120 15 19.71 223 125 12 21.12 167 130 7 22.72 134 135 5 24.43 116 Heinze等[30]将二甲基亚砜(DMSO)作为共溶剂与四丁基氟化铵([B4N]F)结合具有良好的纤维素溶解效果,能在1h溶解聚合度小于600的纤维素。张益波[31]合成了N-丁基-N-甲基吡咯烷甲氧基乙酸盐(N(C4C1)Py][CH3OCH2COO]),并研究了其对MCC的溶解度,结果表明,40℃时MCC的溶解度为1.2%,50℃时MCC的溶解度为15.2%。Ren等[32]合成了9种胆碱类ILs,其中胆碱牛磺酸([Ch][Tau])对小麦秸秆纤维素的溶解性相对较好。侯雪丹[33]通过简单经济的方法合成了[胆碱][氨基酸]ILs,发现该ILs主要通过选择性提取木质素的方式提高底物的酶解效率,而对纤维素结晶结构的作用较弱。
此外,铵基[34]和膦基[35]ILs可溶解水溶液中的纤维素,但是,毒性可能导致环境风险。
1.3 ILs与极性非质子的共溶剂体系
近年来,ILs已成为溶解纤维素的首选溶剂,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纤维素不溶于纯极性溶剂,但溶于IL/有机溶剂溶液。有研究者提出,极性非质子溶剂通过IL阳离子的溶剂化作用,使相应的阴离子更容易与纤维素的氢键相互作用。极性非质子有机溶剂如DMSO[36]、碳酸丙烯酯[37]、γ-戊内酯[38]作为共溶剂和ILs构成的有机电解质溶剂体系(Organic Electrolyte Solutions,OES)能提高纤维素的溶解效率。适量共溶剂的加入不仅不会影响纤维素的溶解效果,反而会提高溶液中的物质扩散运输能力,降低溶解温度以及ILs的用量甚至缩短溶解时间,同时降低溶剂体系的粘度[39]。
任菲等[40]研究了25℃条件下纤维素在DMSO与[EMIM]OAc混合溶液中的溶解性,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随着DMSO浓度的降低,纤维素的溶解度逐渐增加,主要原因是DMSO使[EMIM]OAc发生解离,从而导致游离的阴离子和阳离子增加。这些共溶剂可以通过降低溶剂粘度来加速传质,而不会显著影响阳离子和阴离子之间或ILs和纤维素之间的特定相互作用[41~44]。兰媛等[45]通过向ILs中添加非质子有机溶剂DMSO来增强ILs溶解性能的试验表明,在50℃、ILs与DMSO的质量比为1:1时,ILs对纤维素的溶解性能最强。
张沛然等[46]在不同温度(40、50、60、70 ℃)下用[AMIM]Cl分别与有机溶剂DMF、DMSO、二甲基乙酰胺(DMAc)复配,对竹纤维素桨粕进行溶解。结果表明,ILs与有机溶剂复配能提高竹纤维素桨粕的溶解度,但是如果有机溶剂所占比例过高,其溶解度将降低;当有机溶剂的质量分数为20%时,溶解度最大;有机溶剂为DMSO时,溶解度最大。在这种新型的溶剂中纤维素不需预处理即可完全溶解并通过在水中凝结再生为机械性能良好的纤维素膜。
Liu等[47]合成了[APy]Cl和[EMIM]DEP离子液体,将DMSO加入所合成的ILs中,在105℃时加入活化的松木纤维素,8min内可以溶解3(wt)%的纤维素,且此由纤维素溶液制备的再生纤维素不发生衍生化反应,纤维素的热稳定性没有变化。
Grossereid等[25]合成了具有非常规阴离子的新型双官能化N-氧乙烯-N-磺丙基咪唑基ILs,并考察了其溶解MCC纤维素的能力。结果表明,向ILs溶液中添加极性非质子溶剂,如DMF或DMSO,通过提高纤维素溶解度和缩短溶解时间,成功地促进了纤维素的溶解。
2. ILs溶解纤维素的机理研究
2.1 阴、阳离子与纤维素的作用
对于构成ILs的阴、阳离子的研究表明,在纤维素的溶解过程中,溶解度主要取决于ILs中阴离子的结构,并受其阳离子所影响[2]。ILs中的阳离子仅仅通过氢键、范德华力以及疏水作用等较弱的相互作用对纤维素溶解产生影响[6];ILs溶解纤维素的能力强烈地依赖于阴离子的氢键可接受性[48]。Li等[49]分别建立了4和7链纤维素的两个模型,并用[EMIM]OAc、[EMIM]Cl、[BMIM]Cl和水溶液进行了分子动力学模拟。在[EMIM]OAc中观察到纤维素束的完全溶解,并通过氢键分析进行验证。如图式 4所示,ILs能与纤维素羟基相互作用形成电子给体-电子受体复合物,导致纤维素分子链间氢键网络被破坏。ILs中阴离子一直是良好的氢键受体,阳、阴离子以协同作用溶解纤维素。阳离子最初与纤维素束表面的侧面结合,而阴离子插入束中,并与羟基形成氢键。随着大量阴离子进入纤维素链,阳离子由于与阴离子的强烈相互作用而开始在纤维素链之间插层。大量的离子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分离纤维素链,因此纤维素开始溶解。
图式 4
Wang等[1]的研究表明,ILs中阴、阳离子所形成氢键的碱性及偶极性越强,表明该阴离子对纤维素溶解能力越好。Fukaya等[50]的研究也说明了阴离子(如Cl-、OAc-、HCOO-、烷基磷酸根等)作为氢键受体的能力越强,ILs溶解纤维素能力也越强; 而含有[BF4]-、[PF6]-、[Tf2N]-等弱氢键阴离子的ILs对纤维素不具有溶解性[48]。
Rogers等[14]研究发现,当阴离子均为Cl-时,100℃加热条件下,纤维素在[BMIM]Cl、氯化1-己基-3-甲基咪唑鎓([HMIM]Cl)和氯化1-辛基-3-甲基咪唑鎓([OMIM]Cl)中的溶解度分别是10%、5%和微溶(如表 4所示),这说明随着咪唑环上取代基链长的增加,ILs对纤维素的溶解能力逐渐下降。
表 4
ILs 溶解条件 溶解度/(wt)% [Bmim]Cl 加热(100℃) 10 加热(70℃) 3 [Hmim]Cl 加热(100℃) 5 [Omim]Cl 加热(100℃) 微溶 Lu等[51]制备了13种具有相同[CH3COO]-阴离子但不同阳离子主链和取代基的ILs。结果显示,ILs中的阳离子对纤维素的溶解有显著影响。其阳离子的酸性质子可与纤维素的羟基氧和醚氧形成C-H…O氢键,增加纤维素的溶解度。
Li等[52]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由不饱和阳离子(1-丁基-3-甲基咪唑鎓、1-丁基吡啶鎓、1-丁基-1-甲基吡咯烷鎓、1-丁基-1-甲基哌啶鎓)和乙酸根组成的4种ILs对纤维素束的溶解性能。结果表明,纤维素束只溶解在含有不饱和杂环阳离子的ILs中。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结构因素,不饱和杂环的π电子离域,使阳离子更活跃地与纤维素相互作用,为乙酸根阴离子与纤维素形成氢键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另一个是动态效应,具有饱和杂环的较大体积的阳离子导致阳离子和阴离子的缓慢转移,不利于纤维素的溶解。
Li等[53]以羧酸根为阴离子,分别以1, 8-二氮杂二环[5.4.0]-十一烷-7-烯(DBU)和1, 5-二氮杂二环[4.3.0]-壬烷-5-烯(DBN)为阳离子合成ILs,并进行纤维素溶解度的对比。结果发现,90℃下[DBNH][CH3CH2OCH2COO](18.95(wt)%)在纤维素溶解中的效率低于[DBUH][CH3CH2OCH2COO](22.78(wt)%), 说明阳离子结构中的大环具有促进纤维素溶解的作用。
实验和计算结果都证明纤维素中氢键的破坏是溶解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溶解过程中阴、阳离子协同作用,破坏纤维素内部的氢键网络,纤维素将被重新合成为较不结晶的结构[48]。
2.2 阳离子与纤维素之间的疏水性相互作用
基于对纤维素溶解过程中所涉及相互作用的分析,Lindman等[54]提出ILs的阳离子与纤维素(均为两亲性)之间的疏水性相互作用是促使纤维素溶解的主要因素。对于表 4结果的解释,Rogers等[14]认为是由于取代基链长的增加稀释了氯离子的浓度所致,但张锁江等[55]认为,还可能是因为取代基链长的增加降低了ILs的亲水性,从而会减弱ILs与纤维素之间的亲和性。
此外,具有富电子π系统的咪唑阳离子可与纤维素羟基的氧原子通过非键或π电子相互作用,阻止了纤维素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也促进了纤维素分子的充分溶解[56]。
3. 影响ILs对纤维素溶解性能的因素
纤维素在ILs中的溶解受多因素影响,不仅取决于ILs的有效性和形成氢键的能力,还取决于许多外部因素,如熔化温度、加热方式、ILs的粘度、添加剂和ILs的含水量等[57, 58]。
3.1 内因
3.1.1 ILs氢键酸碱度和ILs的偶极/极化率对纤维素溶解度的影响
ILs溶解纤维素的能力与其氢键碱度和粘度直接相关,氢键碱度越强、粘度越低,溶解能力就越强[59]。Lu等[51]的研究表明,阳离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纤维素在ILs中的溶解度:(1)阳离子杂环中的酸性质子直接与纤维素的氧形成氢键,从而增加纤维素的溶解度;(2)阳离子的极化率及其与阴离子的配位强度通过影响IL阴离子与纤维素形成氢键的能力间接影响纤维素的溶解度,高极化率和弱离子缔合有利于纤维素在ILs中的溶解。
Li等[53]研究了超碱基ILs(Superbase-Derived Ionic Liquids,简称SILs)阳离子对纤维溶解性的影响,结果表明,DBU-SILs对纤维素的溶解度(α=0.49~0.53)优于DBN-SILs(α=0.41~0.42)。α参数可以作为ILs氢键给体能力(氢键酸性)的一个度量指标,并且取决于阳离子结构。阳离子的氢键供体能力越强,α参数值越大,纤维素溶解能力越强。
3.1.2 阳离子化学结构的影响
烷基侧链不能决定纤维素的溶解,但它有助于降低ILs的粘度,从而提高溶解能力[60]。纤维素的溶解度随着阳离子碳链长度的增加而降低[59]。这个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首先,烷基链长的增加会降低ILs的亲水性,从而削弱ILs与纤维素之间的亲和力;第二,取代基链长的增加会增加ILs的尺寸。当ILs的阴离子与纤维素分子链的羟基形成氢键时,阳离子也与羟基氧结合,由于空间位阻效应,阳离子尺寸过大可能会妨碍这种结合,形成氢键的能力变弱[61]。
Li等[53]对于SILs的研究表明,当阳离子为环状基团时,羧酸根阴离子中的给电子基团、小空间位阻基团和短链基团与超碱阳离子中较大的环结合是促进纤维素溶解的合适选择。
3.1.3 纤维素本身结构的影响
一般而言,纤维素的溶解行为受分子质量、结晶度、分子尺寸的影响。纤维素由很多长度不同的线形高分子所组成,即其分子量是不均一、多分散的。纤维素链的平均分子量主要取决于聚合度的大小。人们普遍认为,高浓度聚合物(由于分子缠绕及相互作用)与半结晶聚合物的溶解过程更加缓慢。纤维素分子质量越大,熵值对溶解的影响越弱。由此可知,高分子质量纤维素比低分子质量纤维素更难溶解。
苗娇娇[62]研究了纤维素的DP对其溶解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纤维素的DP的增加,纤维素在[B4N]OAc/DMSO中的溶解度降低。这是由于相同数量的[B4N]OAc/DMSO只能断裂相同数量的氢键,而当纤维素的DP增加时,纤维素分子间、分子内的氢键增加,导致整体溶解度降低。
结晶度也是纤维素溶解度的重要影响因素。X射线衍射研究发现,纤维素大分子的聚集体中包括结晶区和非结晶区,结晶区部分分子排列比较整齐、有规则,链间氢键键能高,分子间结合力强;而非结晶区分子排列不整齐、较疏松,纤维素分子链间可以分隔开,分子间氢键结合数少,这样大量的游离氢键更容易与其他分子的氢键结合,反应性能增强。结晶度越高(结晶区占比例越大),纤维素越不易溶解。Xu等[53]的研究表明,纤维素在SILs中溶解的过程中发生了晶型从结晶度较高的纤维素Ⅰ型到结晶度更低的纤维素Ⅱ型的转变,这可能是由于在溶解再生过程中纤维素链容易缔合或聚集所致。任强等[15]的研究也表明,用[BMIM]Cl和[AMIM]Cl溶解再生的纤维素晶型由纤维素Ⅰ变成了纤维素Ⅱ。
聚合物的两亲性是影响其溶解度的重要因素。Wang等[63]研究表明,纤维素是两亲性分子,通过在纤维素界面上积聚疏水性阳离子,有利于降低表面张力,促进纤维素分散与溶解。
3.2 外因
3.2.1 溶解温度的影响
马浩等[64]测量了不同温度下纤维素在乙酸1, 3-二甲基咪唑鎓([MMIM]OAc)和羟基乙酸1, 3-二甲基咪唑鎓([MMIM]HOCH2COO)两种离子液体中的溶解度,发现溶解温度对纤维素的溶解性有较大的影响。90℃以下,纤维素在两种ILs中只能发生溶胀,随着温度升高,溶解度逐渐增大。表 5的结果还表明,ILs中的阴离子的结构对纤维素的溶解性能有较大的影响[65, 66]。
表 5
ILs 溶解度/% 80℃ 90℃ 100℃ 110℃ 120℃ [C1MIM][CH3COO] 溶胀 4.9 12.1 16.3 19.7 [C1MIM][HOCH2COO] 溶胀 微溶 <0.1 6.8 21.2 3.2.2 加热方式的影响
张沛然等[67]采用油浴和水浴两种加热办法用[AMIM]Cl离子液体溶解竹纤维素桨粕。表 6的实验结果显示,在相同溶解温度下,油浴加热时竹纤维素桨粕溶解速率及溶解度要高于水浴加热时溶解速率及溶解度。
表 6
加热方式 温度/℃ ILs/g 竹纤维桨粕/g 溶解度/% 油浴 40℃ 10.2123 0.0331 0.32 水浴 10.2134 0.0079 0.098 油浴 60℃ 10.1901 0.2504 2.46 水浴 10.2155 0.2318 2.27 油浴 80℃ 10.0240 0.3116 3.09 水浴 10.2427 0.2845 2.78 用微波加热的方式代替传统加热,可以显著提高纤维素在ILs中的溶解度[14]。例如,普通加热至100℃,[BMIM]Cl只能溶解10%的纤维素(DP≈1000);而在相同条件下用微波加热,纤维素的溶解度达到25%[14]。这是因为ILs完全由阴阳离子组成,对微波具有良好的吸收性能,是适合微波加热的介质;此外,微波加热属于立体加热,其传热速度远快于传统加热。
3.2.3 ILs的吸水率
Vitz等[57]的研究表明,吸水率低的ILs更有利于纤维素的溶解。使用未干燥的ILs时,纤维素的溶解度比较低,因此使用前必须仔细干燥所用ILs。研究表明,当水的质量浓度大于ILs的1%时,溶剂性质明显受损,纤维素不再可溶[58]。
4. ILs的回收
研究者从经济和环保的角度出发,研究了ILs的重复利用性。Liu等通过旋转蒸发浓缩液相回收ILs。将回收的ILs重复利用5次,发现第5次循环ILs溶液再生的角蛋白的热稳定性与首次运行再生的角蛋白的热稳定性相同。翟蔚等[68]将分离出再生纤维素膜的水与ILs混合液减压蒸馏后,置于真空干燥器中干燥24h以上除去水分,回收得到ILs,平均回收率为96.20%。Huang等[69]采用减压蒸馏法对催化水解脱脂棉制备纳米纤维素后的[BMIM]HSO4进行回收并重复使用,经过5次循环利用后,ILs的回收率依旧可达90%以上。王均凤等[70]采用NF90纳滤膜可以有效地将[BMIM]Cl从5%浓缩至18.85%,[BMIM]Cl的回收率高达96%以上,大大地降低了能耗。膜预浓缩得到的ILs再进一步采用降膜蒸发的方式,可以有效地将ILs浓缩至95%以上。
5. 结语
ILs溶解纤维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相互作用共同的结果。ILs溶解纤维素的能力主要取决于ILs的极性和氢键结合能力;另外,ILs的阳离子对纤维素的溶解过程也存在特异性,其相互作用主要包括氢键作用、疏水相互作用以及范德华力等。
为了合理设计ILs以实现纤维素的高效溶解,应优先考虑具有强氢键可接受性的阴离子,以及不具有高电负性原子(如氧)的强酸性质子和可产生空间位阻的大体积基团的阳离子。阳离子上的电负性原子的存在会降低质子的酸性,导致溶剂化效率的降低。为了改善纤维素在ILs中的溶解,还可加入DMSO作为共溶剂。有机共溶剂的加入可以降低ILs的粘度,减少溶解所需的时间,提高ILs的溶剂能力,即使在低温下也是如此。总之,ILs无味、无恶臭、无污染、不易燃、易与产物分离、易回收及可反复多次循环使用等优点使它成为传统挥发性有机溶剂的理想替代品,具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
-
-
[1]
Wang H, Gurau G, Rogers R D. Chem. Soc. Rev., 2012, 41(4): 1519~1537. doi: 10.1039/c2cs15311d
-
[2]
Pinkert A, Marsh K N, Pang S S, et al. Chem. Rev., 2009, 109(12): 6712~6728. doi: 10.1021/cr9001947
-
[3]
张锁江, 刘艳荣, 聂毅.轻工学报, 2016, 31(2): 1~14.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zqgyxy201602001
-
[4]
李茂刚, 罗康碧, 李沪萍, 等.化工新型材料, 2018, 46(4): 39~42.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hgxxcl201805012
-
[5]
Cao Y, Zhang R, Cheng T, et al. Appl. Microbiol. Biot., 2016, 101(2): 521~532.
-
[6]
王斌收.功能性纤维素球的制备及应用研究.齐鲁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
[7]
Fink P W, Hans J Pur, Johannes G. Prog. Polym. Sci., 2001, 26(9): 1473~1524. doi: 10.1016/S0079-6700(01)00025-9
-
[8]
雷海斌.福建轻纺, 2017, (8): 33~35.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jqf201708010
-
[9]
王晨, 刘文波.黑龙江造纸, 2018, 46(3): 26~30.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ljzz201803006
-
[10]
Cai J, Zhang L N. Biomacromolecules, 2006, 7(1): 183~189. doi: 10.1021/bm0505585
-
[11]
Wang Y, Liu L, Chen P, et al. Phys. Chem. Chem. Phys., 2018, 20(20): 14223~14233. doi: 10.1039/C8CP01268G
-
[12]
Graenacher C. USP: 1943176, 1934.
-
[13]
Zhu S, Wu Y, Chen Q, et al. Green Chem., 2006, 8: 325~327. doi: 10.1039/b601395c
-
[14]
Swatloski R P, Spear S K, Holbrey J D, et al. J. Am. Chem. Soc., 2002, 124(18): 4974~4975. doi: 10.1021/ja025790m
-
[15]
任强, 武进, 张军等.高分子学报, 2003, (3): 448~450. http://www.cqvip.com/QK/90068X/200303/7911232.html
-
[16]
罗慧谋, 李毅群, 周长忍.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2005, 2: 233~235.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FZC200502058.htm
-
[17]
Hauru L K J, Hummel M, Koschella A, et al. Cellulose, 2014, 21(6): 4417~4481.
-
[18]
李晓严, 刘鑫玉, 郭蔚.功能材料, 2019, 7(50): 7172~7175.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NCL201907031.htm
-
[19]
Zhao D S, Li H, Zhang J, et al. Carbohydr. Polym., 2012, 87(2): 1490~1494. doi: 10.1016/j.carbpol.2011.09.045
-
[20]
Hokayem A K, Hage E R, Svecova L, et al. Molecules, 2020, 25(7): 1629~1647. doi: 10.3390/molecules25071629
-
[21]
Nguyen N A, Kim K, Bowland C C, et al. Green Chem., 2019, 21(16): 4354~4367. doi: 10.1039/C9GC00774A
-
[22]
Isik M, Sardon H, Mecerreyes D. Int. J. Mol. Sci., 2014, 15(7): 11922~11940. doi: 10.3390/ijms150711922
-
[23]
Olivierbourbigou H, Magna L, Morvan D. Appl. Catal. A-Gen., 2010, 373(1): 1~56.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926860X09007030
-
[24]
Lethesh K C, Evjen S, Venkatraman V, et al. Carbohydr. Polym., 2020, 229: 115594 doi: 10.1016/j.carbpol.2019.115594
-
[25]
Grossereid I, Lethesh K C, Venkatraman V, et al. J. Mol. Liq., 2019, 292: 111353. doi: 10.1016/j.molliq.2019.111353
-
[26]
Sixta H, Michud A, Hauru L K J, et al. Nord. Pulp. Pap. Res. J., 2015, 30(1): 43~57. doi: 10.3183/npprj-2015-30-01-p043-057
-
[27]
Raut D G, Sundman O, Su W, et al. Carbohydr. Polym., 2015, 130: 18~25. doi: 10.1016/j.carbpol.2015.04.032
-
[28]
King A W T, Asikkala J, Mutikainen I,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28): 6301~6305. doi: 10.1002/anie.201100274
-
[29]
付林林, 赵地顺, 任培兵, 等.现代化工, 2011, 31(9): 39~42.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DHG201109013.htm
-
[30]
Heinze T, Dicke R, Koschella A, et al. Macromol. Chem. Phys., 2000, 201(201): 627~631.
-
[31]
张益波.低粘度离子液体体系的设计及其溶解生物质高分子的研究.河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32]
Ren H, Zong M H, Wu H, et al. Ind. Eng. Chem. Res., 2016, 55(6): 1788~1795. doi: 10.1021/acs.iecr.5b03729
-
[33]
侯雪丹.用[胆碱] [氨基酸]离子液体预处理木质纤维素生物质的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
[34]
Ohira K, Abe Y, Kawatsura M, et al. ChemSusChem, 2012, 5(2): 388~391. doi: 10.1002/cssc.201100427
-
[35]
Abe M, Fukaya Y, Ohno H. Chem. Commun., 2012, 48(12): 1808~1810. doi: 10.1039/c2cc16203b
-
[36]
Cheng G, Varanasi P, Arora R, et al. J. Phys. Chem. B, 2012, 116(33): 10049~10054. doi: 10.1021/jp304538v
-
[37]
Yuan X, Yuan C P, Shi W T, et al. ChemistrySelect, 2017, 2(13): 3783~3787. doi: 10.1002/slct.201700535
-
[38]
Gale E, Wirawan R H, Silveira R L, et al. ACS Sustain. Chem. Eng., 2016, 4(11): 6200~6207. doi: 10.1021/acssuschemeng.6b02020
-
[39]
张丽华, 徐俊鹏, 王俊钦, 等.武汉大学学报(理学版), 2020, 66(1): 11~22.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filename=WHDY202001002
-
[40]
任菲, 王书军.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暨第十届中美食品业高层论坛: 武汉, 2019.
-
[41]
Xu A R, Cao L L, Wang B J. Carbohydr. Polym., 2015, (125): 249~25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4861715007146
-
[42]
Velioglu S, Yao X, Devemy J, et al. J. Phys. Chem. B, 2014, 118(51): 14860.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5437753
-
[43]
Andanson J, Padua A A H, Gomes M F C. Chem. Commun., 2015, 51(21): 4485~4487. doi: 10.1039/C4CC10249E
-
[44]
Andanson J, Bordes E, Devemy J, et al. Green Chem., 2014, 16(5): 2528~2538. doi: 10.1039/c3gc42244e
-
[45]
兰嫒, 李欣达, 张玥, 等.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 2015, 33(1): 93~97.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lkxygc201501020
-
[46]
张沛然, 吴琼, 杨梦钰, 等.广州化工, 2019, 47(16): 44~47.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ZHA201916022.htm
-
[47]
Liu R, Zhang J, Sun S, et al. J. Eng. Fiber Fabr., 2019, 14: 1~7.
-
[48]
Li Y, Wang J J, Liu X M, et al. Chem. Sci., 2018, 9(17): 4027~4043. doi: 10.1039/C7SC05392D
-
[49]
Li Y, Liu X M, Zhang S J, et al. Phys. Chem. Chem. Phys., 2015, 17(27): 17894~17905. doi: 10.1039/C5CP02009C
-
[50]
Fukaya Y, Hayashi K, Wada M, et al. Green Chem., 2008, 10(1): 44~46. doi: 10.1039/B713289A
-
[51]
Lu B L, Xu A R, Wang J J. Green Chem., 2014, 16(3): 1326~1335. doi: 10.1039/C3GC41733F
-
[52]
Li Y, Liu X M, Zhang Y Q, et al. ACS Sustain. Chem. Eng., 2017, 5(4): 3417~3428. doi: 10.1021/acssuschemeng.7b00073
-
[53]
Li X, Li H C, Ling Z, et al. Macromolecules, 2020, 53(9): 3284~3295. doi: 10.1021/acs.macromol.0c00592
-
[54]
Lindman B, Karlstrom G, Stigsson L. J. Mol. Liq., 2010, 156(1): 76~81. doi: 10.1016/j.molliq.2010.04.016
-
[55]
张锁江, 吕兴梅, 等.离子液体——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应用.第二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326~357.
-
[56]
李昌志, 王爱琴, 张涛.化工学报, 2013, 64(1): 182~197. http://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44326293
-
[57]
Vitz J, Erdmenger T, Haensch C, et al. Green Chem., 2009, 11(3): 417~424. doi: 10.1039/b818061j
-
[58]
Mazza M, Catana D, Vacagarcia C, et al. Cellulose, 2009, 16(2): 207~215. doi: 10.1007/s10570-008-9257-x
-
[59]
Zhang J M, Wu J, Yu J, et al. Mater. Chem. Front., 2017, 1(7): 1273~1290. doi: 10.1039/C6QM00348F
-
[60]
André Pinkert K N M, Pang S S. Ind. Eng. Chem. Res., 2010, 49(22): 11121~11130. doi: 10.1021/ie1006596
-
[61]
李垚.离子液体溶解生物质的分子模拟研究.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2017.
-
[62]
苗娇娇.季铵盐离子液体体系中纤维素溶解机理及应用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
-
[63]
Wang Y, Liu L, Chen P, et al. Phys. Chem. Chem. Phys., 2018, 20(20): 14223~14233. doi: 10.1039/C8CP01268G
-
[64]
马浩, 廖春燕, 樊梅林, 等.应用化学, 2018, 35(4): 449~456. 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yyhx201804010
-
[65]
Zhao Y L, Liu X M, Wang J J, et al. Carbohydr. Polym., 2013, 94(2): 723~730. doi: 10.1016/j.carbpol.2013.02.011
-
[66]
Yuan X M, Cheng G. Phys. Chem. Chem. Phys., 2015, 17(47): 31592~31607. doi: 10.1039/C5CP05744B
-
[67]
张沛然, 吴琼, 李钊, 等.山东化工, 2019, 48(13): 42~46. 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shandong-chemical-industry_thesis/0201272837104.html
-
[68]
翟蔚, 陈洪章, 马润宇.北京化工大学学报, 2007, 34(2): 138~141.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bjhgdxxb200702007
-
[69]
Huang J, Hou S N, Chen R Y. Bioresources, 2019, 14(4): 7805~7820.
-
[70]
王均凤, 聂毅, 王斌琦等.化工学报, 2019, 70(10): 3836~3846.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gxb201910017
-
[1]
-
表 1 纤维素在[MMIM]+[MMP]-中完全溶解所需温度和时间
Table 1. The temperature and time of cellulose completely dissolved in [MMIM]+[MMP]-
温度/℃ 70 80 90 100 110 120 时间/min 160 128 120 108 97 75 表 2a 纤维素在[MMIM]DMP中的溶解条件
Table 2a. Dissolution conditions of cellulose in [MMIM]DMP
溶解温度/℃ 70 80 90 100 110 120 溶解时间/min 400 320 300 270 243 188 表 2b 纤维素在[EMIM]DEP中的溶解条件
Table 2b. Dissolution conditions of cellulose in [EMIM]DEP
溶解温度/℃ 70 80 90 100 110 120 溶解时间/min 100 20 11 6 4 2 表 3 纤维素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性能
Table 3. The dissolution properties of cellulose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溶解温度/℃ 溶解时间/min 溶解度/% 再生纤维素的DP 115 36 14.72 256 120 15 19.71 223 125 12 21.12 167 130 7 22.72 134 135 5 24.43 116 表 4 可溶性纤维素桨粕在ILs中的溶解度
Table 4. The solubility of bamboo cellulose pulp in different ILs
ILs 溶解条件 溶解度/(wt)% [Bmim]Cl 加热(100℃) 10 加热(70℃) 3 [Hmim]Cl 加热(100℃) 5 [Omim]Cl 加热(100℃) 微溶 表 5 纤维素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
Table 5. The solubility of cellulose in different temperature
ILs 溶解度/% 80℃ 90℃ 100℃ 110℃ 120℃ [C1MIM][CH3COO] 溶胀 4.9 12.1 16.3 19.7 [C1MIM][HOCH2COO] 溶胀 微溶 <0.1 6.8 21.2 表 6 不同加热方式下竹纤维素桨粕溶解度对比
Table 6. Comparison of solubility of bamboo cellulose pulp by heating method
加热方式 温度/℃ ILs/g 竹纤维桨粕/g 溶解度/% 油浴 40℃ 10.2123 0.0331 0.32 水浴 10.2134 0.0079 0.098 油浴 60℃ 10.1901 0.2504 2.46 水浴 10.2155 0.2318 2.27 油浴 80℃ 10.0240 0.3116 3.09 水浴 10.2427 0.2845 2.78 -

 扫一扫看文章
扫一扫看文章
计量
- PDF下载量: 121
- 文章访问数: 3866
- HTML全文浏览量: 1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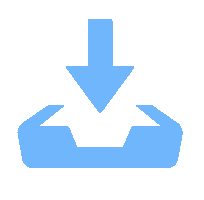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