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49
2016-02-22 收稿, 2016-03-28 接受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史青年人才研教特别支持项目(Y52901YEA2)资助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19世纪中叶,西方化学传入中国以后,一批重要的化学译著相继问世。这些译著中都翻译了一些化学名词。进入20世纪以后,关于化学名词的方案及讨论多了起来。人们意见不一,译名混乱。直到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颁布《化学命名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中文化学名词才有了统一的标准。《原则》确立的许多名词一直沿用至今。这些名词在用字上大都是根据这样一条命名总则来拟定的:“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1]。我们熟知的苯、萘、蒽、菲等名词就是音译的,占绝大多数。少部分名词,如烷、烯、炔,是意译的。考虑到《原则》摈弃了苯、萘、蒽、菲等的各种历史译名,而创造了全新的音译名。我们或许会问:《原则》为何要采纳烷、烯、炔这三个旧有的意译名呢?为什么不对烷、烯、炔也拟定全新的音译名呢?这其中是否存在合理性?
本文以历史上重要有机化合物中文命名方案提出的烷、烯、炔译名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这些译名的特点,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20世纪初以前,对于有机物的命名往往采取将西文名词的所有音节完全音译过来的办法,繁冗至极。1905年,杜亚泉在《化学新教科书》中对于开链烃的中文命名首先使用了单字音译方法[2]。具体来讲,根据甲烷(methane)、乙烯(ethylene)和乙炔(acetylene)的西文名称之首音,他把三者分别音译为迷、依、阿。以此为基础,烷烃、烯烃、炔烃的中文名称分别由“米”字旁、“亻”旁、“阝”旁和一个音译汉字组成。如: (乙烷)、
(乙烷)、 (丙烷)、
(丙烷)、 (丁烷);
(丁烷); (丙烯)、侼(丁烯);
(丙烯)、侼(丁烯); (丙炔)等。相较于将西文名称的所有音节全部音译的方法,这种命名思路有所进步。但烷烃、烯烃、炔烃的数目极其庞大,一一拟定具体的名称并不现实。
(丙炔)等。相较于将西文名称的所有音节全部音译的方法,这种命名思路有所进步。但烷烃、烯烃、炔烃的数目极其庞大,一一拟定具体的名称并不现实。
1908年,虞和钦于《有机化学命名草》中提出了第一个系统的有机物中文命名方案。其命名特点是采用意译的方法命名且不造新字。对于烷、烯、炔,虞和钦分别命名为矫质、羸质、亚羸质。同年稍后,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提出的有机物命名方案中将烷、烯、炔分别称为足、欠、 ,也没有造新字。1920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创制了烷、烯、炔三个译名[3]。关于烷、烯、炔的种种其他译名也在这个时期提出。1932年教育部颁布《原则》,中国化学界开始使用统一的化学名词。烷、烯、炔三个名称就此确立,没有再更改过,至今沿用。
,也没有造新字。1920年,科学名词审查会创制了烷、烯、炔三个译名[3]。关于烷、烯、炔的种种其他译名也在这个时期提出。1932年教育部颁布《原则》,中国化学界开始使用统一的化学名词。烷、烯、炔三个名称就此确立,没有再更改过,至今沿用。
为了论述方便,把1908~1932年提出的有机物命名方案对于烷(甲烷)、烯(乙烯)、炔(乙炔)的命名列于表 1。
从表 1可看出,烷、烯、炔的各种译名,不外乎有这几个特点:使用单个汉字或多个汉字命名、不造新字或者创造新字命名、采用意译法或音译法命名。而我们现今所采用的烷、烯、炔三个译名具有的特点是:使用单个汉字命名、采用旧有汉字不造新字命名、采用意译法命名。下面分析为什么译名烷、烯、炔最后被《原则》采纳。
从学理角度来讲,相比于采用多个汉字来命名有机物的类名,用单字来命名的译名明显更有优势。因为有机化合物命名复杂,对应的中文名称往往字数繁多,如果用多个汉字来指称有机物的类名,那么整个有机物的名称必然繁琐。根据表 1,采用多个汉字命名的有虞和钦、教育部(1915年)、陶烈、恽福森、郑贞文(1920年)、张修敏、中国化学研究会。陈文哲用单个汉字踬和 命名烷和烯,用两个汉字亚
命名烷和烯,用两个汉字亚 命名炔。除此之外,其余方案都用单个汉字命名。它们是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马君武、梁国常、陈庆尧、科学名词审查会、杜亚泉(1920年)、郑贞文与杜亚泉(1924年)、吴承洛、䣝恂立、《原则》的方案。
命名炔。除此之外,其余方案都用单个汉字命名。它们是中国化学会欧洲支会、马君武、梁国常、陈庆尧、科学名词审查会、杜亚泉(1920年)、郑贞文与杜亚泉(1924年)、吴承洛、䣝恂立、《原则》的方案。
采用多个汉字命名的方案不具优势,因此接下来分析为什么在上面采用单个汉字命名的众多方案中,烷、烯、炔三个译名最后被《原则》采纳。上述方案中,科学名词审查会、杜亚泉(1920年)、郑贞文与杜亚泉(1924年)、吴承洛、《原则》使用的译名都是烷、烯、炔。因此,把这几个方案都算作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方案来讨论。下面分析欧洲支会、马君武、梁国常、陈庆尧、科学名词审查会、䣝恂立提出的译名。
先从是否拟制酉安新造字的角度来考察上面6个方案。从表 1可看出,马君武与梁国常的方案有采用新造字。马君武的、酉因是新造字,醂是旧有汉字。梁国常的三个译名 、
、 都是新造字。欧洲支会、陈庆尧、科学名词审查会、䣝恂立的方案则没有拟制新字。创制新字命名的还有陈文哲的
都是新造字。欧洲支会、陈庆尧、科学名词审查会、䣝恂立的方案则没有拟制新字。创制新字命名的还有陈文哲的 、亚
、亚 ,中国化学研究会的
,中国化学研究会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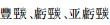 。其中
。其中 二字为新造字。除此以外,其余所有方案都没有创造新字。也就是说,在烷、烯、炔的译名上,绝大多数方案都选择了不造新字。
二字为新造字。除此以外,其余所有方案都没有创造新字。也就是说,在烷、烯、炔的译名上,绝大多数方案都选择了不造新字。
那么,对于造新字的译名与利用旧有汉字的译名,究竟哪个更具优势?这不能一概而论。
从有机化合物中文命名的历史来看,绝大多数方案都创造了新字。虞和钦“不创新字为宗”的做法几乎没有被后来的方案采纳。虽然如此,绝大多数方案提出者仍然是尽量不造新字,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旧有汉字命名时,才创制新字。譬如,欧洲支会和陈庆尧的方案偏向于使用生僻的古字来命名,其所造新字往往是为保持其有机名词体系的一贯性不得已而造,且这些新字都注意仿照生僻字字形拟制,以显得并不像新字[21]。二者认为在烷、烯、炔的命名上可以利用已有汉字,因此并不拟造新字。吴承洛的方案“以不造新字为主,创造新字为附”[18],虽然不排斥造新字,但更愿意支持利用固有汉字的译名烷、烯、炔。䣝恂立对于造字的态度非常鲜明:“用字须不涉怪僻,须易于发音”,“宁造字典所无,不合古义,然易识别之新字。而决不牵强附会,引经据典,为取字之标准。”[22]他拟造的新字有 (nitriles)、
(nitriles)、 (hydrazones)、
(hydrazones)、 (carane)、
(carane)、 (terpane)等。即便如此,对于烷、烯、炔的命名,䣝恂立并没有“造字典所无”之新字。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固有汉字浣、
(terpane)等。即便如此,对于烷、烯、炔的命名,䣝恂立并没有“造字典所无”之新字。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固有汉字浣、 、決是合适可用的译名。
、決是合适可用的译名。
在烷、烯、炔的各种译名中,梁国常的译名 、
、 在造字上极为激进大胆。这表现在这些新字的字形与中国旧有汉字的字形并不相符。这个特点决定了梁的名词很难与中国文字融合,从而不被接纳。
在造字上极为激进大胆。这表现在这些新字的字形与中国旧有汉字的字形并不相符。这个特点决定了梁的名词很难与中国文字融合,从而不被接纳。
因此,就造新字的译名与利用旧有汉字的译名而论,如果二者都没有重大缺陷,那么利用旧有汉字的译名更具优势。就烷、烯、炔的译名来说,梁国常的造新字的译名 、
、 明显不具优势。而马君武的译名
明显不具优势。而马君武的译名 、醂中
、醂中 是新造字,相较于其他名词,没有特别明显的缺陷。
是新造字,相较于其他名词,没有特别明显的缺陷。
不过这三个名词是用单字音译法命名的。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对于化学物质的中文命名用字,是音译好,还是意译好?这也需要视情况而定。
从表 1可看出,除马君武的 、醂以外,其余所有译名都是意译名。在旧有译名大都支持意译名时,一般而言,音译名不具优势。但我们知道,在重要芳香族化合物与杂环化合物母核的中文命名用字上,虽然旧有译名大都采用意译名,有时兼用象形法,音译名占很少数,《原则》仍然没有采用旧有译名,而是创制了全新的音译名苯、萘、蒽、菲等。这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原则》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在用字上采用意译时,各方案在选择翻译哪种“意”时不能达成统一,即使翻译的“意”是一致的,用字也可以五花八门。在用字上采用象形方法,以描摹有机物的结构式,也并不妥当,因为对有机物结构式采取不同的写法,用来象形的汉字必然不同。相较而言,在用字上采取音译的方法,在操作上相当方便,只需遵循徐寿提出的元素汉译名的单字音译原则,翻译西文名称之首音或次音再加上适当的偏旁即可[23]。这个音的标准可以规定为官话音,这样很容易统一。
、醂以外,其余所有译名都是意译名。在旧有译名大都支持意译名时,一般而言,音译名不具优势。但我们知道,在重要芳香族化合物与杂环化合物母核的中文命名用字上,虽然旧有译名大都采用意译名,有时兼用象形法,音译名占很少数,《原则》仍然没有采用旧有译名,而是创制了全新的音译名苯、萘、蒽、菲等。这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原则》之所以如此处理,是因为在用字上采用意译时,各方案在选择翻译哪种“意”时不能达成统一,即使翻译的“意”是一致的,用字也可以五花八门。在用字上采用象形方法,以描摹有机物的结构式,也并不妥当,因为对有机物结构式采取不同的写法,用来象形的汉字必然不同。相较而言,在用字上采取音译的方法,在操作上相当方便,只需遵循徐寿提出的元素汉译名的单字音译原则,翻译西文名称之首音或次音再加上适当的偏旁即可[23]。这个音的标准可以规定为官话音,这样很容易统一。
不过具体到烷、烯、炔的译名,音译名的确不比意译名有优势。因为从表 1的意译名来看,无论是哪个译名,所翻译的“意”都是一致的。即用汉字分别表达出烷、烯、炔中碳碳单键、碳碳双键、碳碳叁键的饱和、不饱和与更不饱和之“含义”。譬如,虞和钦认为烷烃“化合力已甚饱足,不能再与他物结合为附加化合体,故名曰矫质,取中立不倚之义也。”烯烃“因其化合未饱之故,名之曰羸质。”炔烃“较羸质又少轻二原子者,称曰亚羸质。”[4]陈文哲的踬、 、亚
、亚 ,梁国常的
,梁国常的 、
、 ,中国化学研究会的
,中国化学研究会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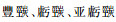 等,都用不同的汉字表达了烷、烯、炔中碳碳键依次递减的不饱和程度。
等,都用不同的汉字表达了烷、烯、炔中碳碳键依次递减的不饱和程度。
如果说音译名的优势在于所译之音可选用官话音从而标准统一,那么,对于烷、烯、炔的译名来说,由于所译之“意”高度一致,在旧有译名都采用意译名时,当然是意译名更有优势。因此,马君武的音译名不具优势。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译同一个意的不同意译字来说,哪个译名更有优势呢?
可以看到,欧洲支会将烷、烯、炔分别命名为足、欠、 ,足与欠是常见字,
,足与欠是常见字, 是生僻字。将常见字用于化学物质的命名,并不适当,因为容易与它们的日常含义发生歧义。
是生僻字。将常见字用于化学物质的命名,并不适当,因为容易与它们的日常含义发生歧义。
陈庆尧选用柕、枵、枯三字命名烷、烯、炔的理由是:“柕字字典同楙,取其木盛之义,用作已饱和炭轻族之总称。”“枵字字典音嚣,取其木空之义,用以代表炭轻族之有一个双价标者。因本族虽不饱和未达极点也。”“枯字字典酷乌切,取其木槁之义,与含有一个三价标之炭轻族为最不饱和之事实,(二炭以三价结合为达不饱和之极点)适相吻合。故以名之。”[14]
烷、烯、炔三字由科学名词审查会于1920年提出。三者都是旧有汉字,统一使用了火旁,表示“炭质之易燃”。“完旁表示完全之意,用作已饱和炭轻族之总称。”“希旁以表希少,用以代表炭轻族之有一个双价标者(Double bond)。”“夬旁以表欠缺之意,用以代表炭轻族之有一个三价标者。”[24]烷字受到1915年教育部颁布的名词“完质”的影响。《原则》采纳了烷、烯、炔三字,其注释是烷“从完,示化合价完足之意”,烯、炔“从希从夬,示化合价希少或缺乏之意”,三字“皆会意”。[25]
䣝恂立使用浣、 、決三字。用水旁不用火旁的理由是,䣝恂立规定“油族(开鍊化合物)之单物名称,或基名,从氵”,而“
、決三字。用水旁不用火旁的理由是,䣝恂立规定“油族(开鍊化合物)之单物名称,或基名,从氵”,而“ 族(异质轮形化合物)之单物名称,或基名,从火”。[26]
族(异质轮形化合物)之单物名称,或基名,从火”。[26]
究竟哪个译名更合适呢?在烷、烯、炔的各种意译名中,面临的问题与译同一个“音”的各种音译名的问题相同。比如要考虑到笔画的繁简,字形是否生僻或过于常用等等因素。陆贯一认为烯、炔就不太恰当,因为细究起来,二字之声旁希与夬虽“足以示未饱和之意”,“但未能示不饱和之程度”,因此该二字容易混淆。他提议将烷字减去两笔,用字表示烯烃。再把字减去两笔,并将宀头移于火上,则成灾字,以命名炔烃。陆氏认为用、灾二字代替烯、炔,“不特较有意识,且笔划简单,便于笔述。”[27]䣝恂立认为他所建议的欠字比烯字恰当,理由是“欠字笔画较希字为少,且欠于稍减而胜于缺之义,似较希合用。”[28]
然而,在要考虑的诸如笔画繁简的种种因素之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译名是否使用较久。与其他译名相比,译名烷、烯、炔就具有通行较久的优势。大概在1922年后,郑贞文编辑、参与编订或校订的化学书籍都采纳了这三个名词,如与杜亚泉共同编纂的《有机化学》(1924)、《现代初中教科书化学》(1925)、《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化学》(1928)、孔庆莱译的《有机化学》(1928)、《新时代高中教科书化学》(1930)、《有机化学概要》(1930)等。由于郑贞文1918~1932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译所编辑、理化部主任等职,该馆出版的化学书籍大都采纳了他的化学名词。许多书籍重印至四、五十次。商务印书馆又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之一,因此译名烷、烯、炔流行广泛便是自然而然了。
相较而言,浣、 、決三个名词仅在1931年才提出。虽然这三个字在表意及用字之规整上并不比烷、烯、炔三字为差,但也不占更多的优势。既然烷、烯、炔较其他名词而言并无重大缺点,且又通行较久,那么当然是译名烷、烯、炔最后得以存留。
、決三个名词仅在1931年才提出。虽然这三个字在表意及用字之规整上并不比烷、烯、炔三字为差,但也不占更多的优势。既然烷、烯、炔较其他名词而言并无重大缺点,且又通行较久,那么当然是译名烷、烯、炔最后得以存留。
乍看之下,烷、烯、炔的中文命名历史与苯、萘、蒽、菲等芳香母核的中文命名历史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即二者的译名都以意译名为主。仔细琢磨,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烷、烯、炔的各种意译名翻译的“意”高度统一,即分别译出碳碳单键、碳碳双键、碳碳叁键的饱和、不饱和与更不饱和之“意”。而苯、萘、蒽、菲等各种意译名表达的“意”五花八门,正如䣝恂立所言“何不规则之甚也”。因此,对于苯、萘、蒽、菲等芳香母核的命名来说,选择音译名,规定所译之音与官话音相符,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对于烷、烯、炔的命名,由于所译之“意”不存在分歧,自然无需采用音译名了。由于译名烷、烯、炔提出较早,使用较久,且并无重大缺陷,相较于其他意译名更有优势,于是便在《原则》中得到采纳,一直沿用至今。
烷、烯、炔的命名历史启示我们,在化学物质的命名用字上,如果对于化学物质名称所表达的“意”能够达成一致,那么意译名比音译名更具优势。毕竟,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正是由于汉字的这一特性,中国化学家在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取字上孜孜以求于意译方法,同时不能摆脱该方法所造成的困境,即对翻译何种“意”难以统一。可以说,烷、烯、炔这样的案例在中文化学命名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元素的中文命名,我们遵循且继续遵循由徐寿所创制的单字音译原则。
 2016,
Vol. 79
2016,
Vol. 79 Issue (7): 667-670, 666
Issue (7): 667-670, 666 2016,
Vol. 79
2016,
Vol. 79 Issue (7): 667-670, 666
Issue (7): 667-670, 666